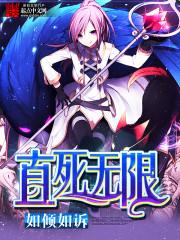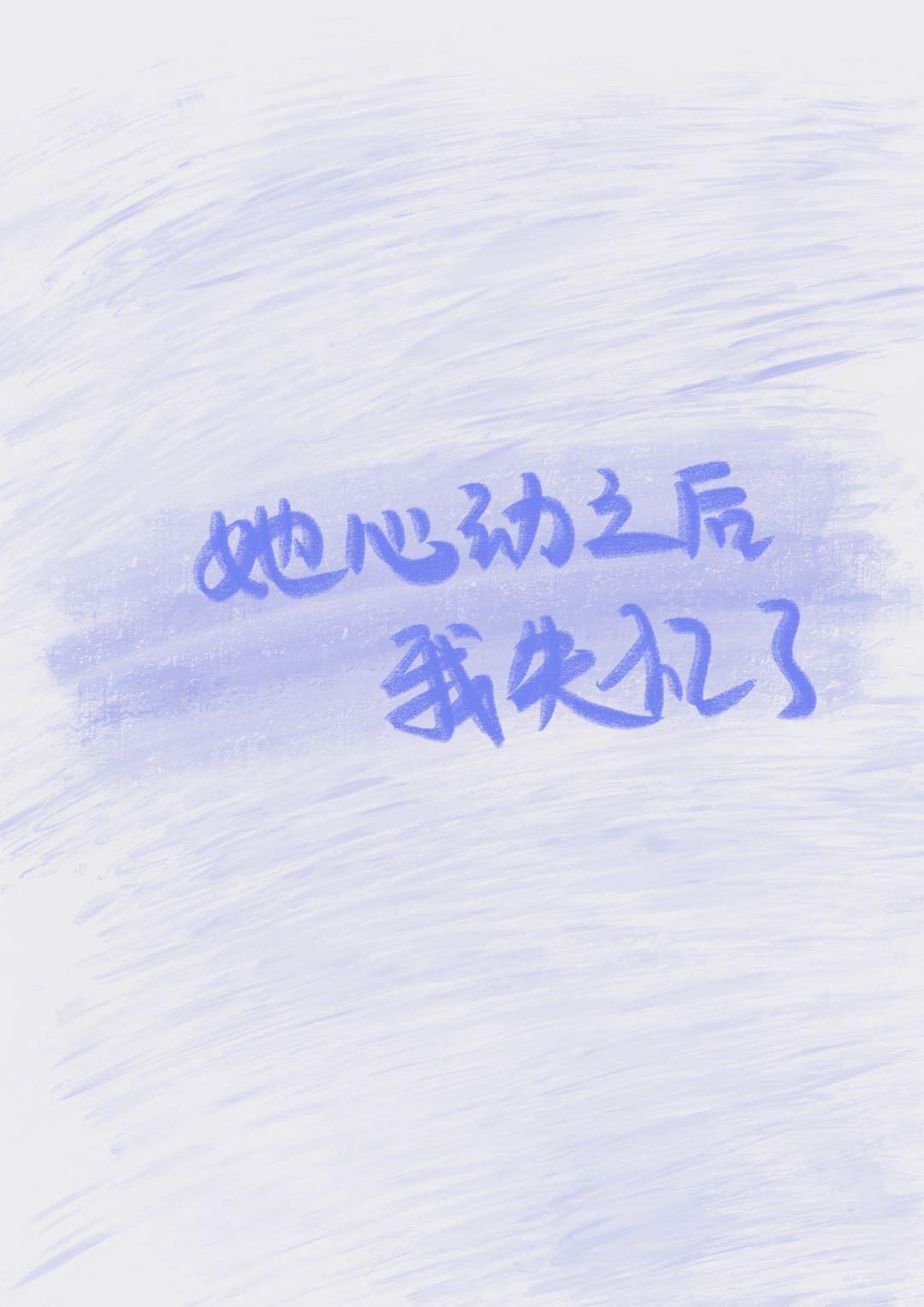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当过明星吗,你就写文娱? > 第二百一十一章 收益更高的打法(第3页)
第二百一十一章 收益更高的打法(第3页)
三天后,文化部召开专题研讨会,主题定为“娱乐过度商业化背景下的声音伦理”。余惟作为主讲人之一,提交了一份长达两万字的调研报告,列举近五年爆款歌曲中“虚假叙事”的典型案例:农民工之子其实家境优渥、外卖小哥实为富二代体验生活、底层奋斗故事由编剧团队杜撰……
“我们不再需要听众,”他在会上直言,“我们只需要观众。而当所有人忙着扮演别人的时候,谁还在做自己?”
会议最终促成三项改革:一是建立“原创声音溯源机制”,要求所有公共传播作品标注采样来源;二是设立“非表演性声音奖项”,表彰未经修饰的真实记录;三是推动主流媒体增加“普通人时段”,每晚黄金时间播出五分钟民间音频故事。
风波暂歇,余惟却并未停下脚步。
秋天来临,他北上探访黄河岸边的最后一批纤夫。这群老人平均年龄六十八岁,曾靠人力拉船穿越激流险滩。如今河道改道,船只机械化,他们的身影几乎消失在历史尘埃中。
见面那天,老人们穿着褪色的粗布衫,背脊弯曲,手掌布满厚厚茧壳。最年长的一位九十岁,已无法言语,只能用手指在桌面上缓缓划动,模拟当年拉绳的动作。
余惟跪在地上,将麦克风贴近他的手掌。
那一晚,他采集到了一组奇特的音频:风吹过废弃码头的呜咽、旧缆绳摩擦石墩的吱呀、老人呼吸间隐约浮现的号子残片。他把这些声音编织进交响诗《河骨》,并在结尾加入一段空白静默??整整一分钟,什么也不放。
“这是留给未来的提问。”他在演出说明中写道,“当我们把所有劳动都交给机器,那些曾经支撑江河奔流的人体节拍,是否还能被记住?”
《河骨》在国家音乐厅上演当晚,台下坐着数十位退休航运工人。当最后一分钟静默结束,全场自发响起掌声,持续十一分钟??正好是当年一段典型纤夫号子的时长。
冬至那天,余惟回到北京。胡同口的老槐树挂满了冰凌,像垂落的水晶铃铛。他推开工作室的门,发现桌上放着一封信,寄自青海湖畔的一所观鸟站。
信是一个志愿者写的,附着一段U盘录音。她说每年冬天都有上千只斑头雁迁徙至此,科研人员为它们佩戴追踪器,记录飞行轨迹。去年,一只编号G-17的雁在途中坠亡,设备却仍在传输数据。他们打开音频文件才发现,最后三小时里,除了风声,还有极其微弱的鸣叫循环往复,像是呼唤同伴,又像告别。
“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坚持录到最后,”信中写道,“但它让我们明白,即使注定坠落,也要留下声音。”
余惟将这段音频剪辑进新年特别企划《未完成的迁徙》,并与天文台合作,把声波转化为可视光谱,投射在跨年晚会的夜空中。那一刻,亿万观众抬头望见的不只是烟花,还有一条由声音绘成的候鸟航线,蜿蜒穿越星辰。
零点钟声敲响时,陈屿打来电话:“你知道吗?今夜全国有两千多个社区自发组织了‘静听一刻’活动。人们关掉电视,打开窗户,只为听听这一年最后的风声。”
余惟站在阳台上,望着城市渐次熄灭的灯火,轻声回应:“这不是我的功劳。我只是搭了个桥,让他们听见了彼此。”
新的一年,他启程前往西南边境的雷区排爆部队驻地。那里每一寸土地都可能吞噬生命,每位战士脚下都踏着倒计时。出发前,战友劝他别去:“太危险,而且……他们不会说话。”
“正因为不能轻易开口,”余惟说,“才更要让他们的沉默被理解。”
抵达当晚,年轻排爆手们围坐在火堆旁,终于有人低声开口:“每次穿上那身装备,我都觉得像在给自己穿寿衣。但我们必须去,因为后面是村庄,是学校,是孩子上学的路。”
余惟录下了这些话语,也录下了拆卸引信时金属碰撞的冰冷脆响。回程途中,他决定做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将整段录音制成黑胶唱片,限量发行九百张??象征中国现存九百名专业排爆人员。每张唱片封套内侧印有一行小字:“播放这张唱片时,请记住,有人正用生命换取你此刻的安全。”
唱片发售五分钟售罄。买家纷纷留言:“我会好好听,也会好好活。”
而在遥远的边陲营地,战士们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从音箱里传出时,有人默默敬礼,有人伏地痛哭。班长红着眼眶说:“我们不怕死,只怕死了也没人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死。”
余惟留下了最后一句话:“你们的名字,会跟着这些声音一起活下去。”
2026年清明,一座新型纪念馆在南京落成,名为“无声纪念碑”。馆内无雕像,无碑文,只有一千个耳机座,循环播放《人间和声》系列作品。参观者戴上耳机,便能听见殡仪馆的夜雨、矿井深处的咳嗽、盲童指尖的颤音、戍边战士升旗的呼号……
开馆首日,一位老兵带着孙子前来。听完一段抗战老兵口述后,孩子仰头问:“爷爷,勇敢是不是一定要打仗?”
老人抚摸他的头:“不,孩子。勇敢是哪怕没人看见,你也坚持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同一时刻,余惟正坐在一辆绿皮火车上,驶向未曾命名的下一站。窗外山峦起伏,铁轨延伸至雾霭深处。他打开笔记本,写下一行新标题:
**《下一站,是你》**
他知道,只要还有人在沉默,他的旅途就不会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