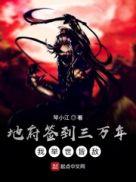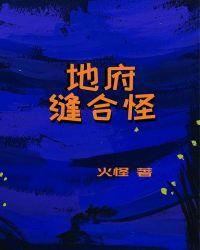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当过明星吗,你就写文娱? > 第二百一十二章 世纪大和解(第1页)
第二百一十二章 世纪大和解(第1页)
这小子在干嘛,现在是码字的时候吗?
不说十万火急吧好歹是争分夺秒,都火烧眉毛了还有心思写小说,也不知道他是心态好还是有信心。
这么从容的吗,不愧是他。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早就已经写完。。。
绿皮火车在山间穿行,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像某种古老的节拍器,一下一下敲打着余惟的神经。他靠窗坐着,笔记本摊在膝上,笔尖悬停在那行字??“《下一站,是你》”??迟迟未落。窗外的雾气时聚时散,仿佛大地在呼吸,而他的思绪也如这云烟般缭绕不散。
他想起昨天离开排爆部队时,一名战士递给他一枚锈迹斑斑的弹壳,说:“这是我们从雷区清理出来的最老的一枚,1979年的。它埋了快五十年,今天才被听见。”余惟接过那枚弹壳,沉甸甸的,像是承载了一整段被遗忘的历史。他在笔记本里记下这句话:“有些声音,等了几十年才被人听见。”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陈屿发来的消息:“南京馆今日参观人数破万。有个聋哑学校的孩子听完后用手语说:‘原来沉默也可以唱歌。’”
余惟轻轻笑了,把这句话抄进本子,又翻到前一页,上面密密麻麻写着这些年他走过的地方、听过的声音、见过的人。云南山村的小女孩叩击水泥柱的三声;女工哼出的第一句潮汕童谣;服刑者讲述那一刀前拨打七次无人接听的电话;纤夫手掌划过桌面的轨迹;斑头雁最后三小时的鸣叫循环……这些声音原本都该消逝在风里,可它们被留下来了,编织成一张巨大的网,网住了这个时代最容易被忽略的生命震颤。
火车缓缓驶入一个小站,站名牌上写着“长岭镇”。站台上只有两个卖烤红薯的老妇人,一个穿着褪色蓝布衫的男人蹲在角落抽烟。余惟忽然起身,拎起背包就下了车。他不知道自己为何停下,就像当初踏上云南山路时也不知会遇见一群孩子写歌一样。但他相信,每一个偶然的停留,都是某种声音在召唤。
镇子不大,青石板路被雨水泡得发黑,两旁是低矮的砖房,墙上贴着泛黄的春联和褪色的政策标语。他走着走着,听见一阵断续的笛声,从巷子深处传来。那声音不成调,却有种执拗的坚持,像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着走路。
循声而去,他在一间破旧诊所门口停下。门楣上挂着块木牌,字迹模糊,依稀能辨“卫生所”三字。院子里,一位老人坐在竹椅上,手里握着一支竹笛,正闭眼吹奏。他满脸皱纹,右腿空荡荡地搭在小凳上,裤管用别针固定。笛声忽高忽低,有时卡住,又重新接上,像在回忆一首几乎忘光的曲子。
余惟没有打扰,只是静静站在院外听着。一曲终了,老人睁开眼,目光落在他身上,竟不惊讶,只问:“你也来找声音的?”
余惟点头:“您怎么知道?”
老人笑了笑:“这两年,来这儿的人多了。都是听说‘会说话的听诊器’的事。”
“听诊器?”余惟皱眉。
老人指了指屋里:“进来吧,我给你听听。”
屋内陈设简陋,药柜积灰,墙上挂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年轻医生站在村口,怀里抱着个孩子,身后是一群村民。照片下方写着“1976年长岭赤脚医生合影”。
“我叫周志民,”老人说,“以前是这儿的医生。四十八年前,我在山洪里救了个孩子,自己丢了条腿,也丢了行医资格。后来这卫生所就荒了。”
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只老式听诊器,铜头已氧化发绿。“但这东西没丢。”他说,“我一直用它听人的身体,也听这片土地。”
余惟接过听诊器,疑惑地看着他。
“你试试,”周志民说,“不是听人,是听墙。”
余惟迟疑地将耳塞戴上,胸件贴在斑驳的土墙上。起初只有寂静,接着,一丝极细微的震动传来??像是心跳,又像脉搏,在墙体深处缓缓跳动。他屏息凝神,那震动渐渐清晰:有咳嗽声、婴儿啼哭、老人叹息、女人低声祈祷……甚至还有当年广播喇叭里播放的《东方红》片段,断断续续,如同记忆残片。
“这……怎么可能?”余惟震惊。
“不是不可能,”周志民平静地说,“是积累。几十年来,这墙听过太多人生病时的呻吟、临终前的遗言、产妇的尖叫、孩子的第一声哭。声音不会消失,它们藏在砖缝里,渗进泥土中。只要有人愿意听,它们就会回来。”
余惟猛地想起什么:“您是不是……曾经给村民录音?”
周志民摇头:“我没设备。但我教他们说话??生病时不要忍着痛,难过时不要憋着眼泪,想骂就骂,想唱就唱。我说,疼也是一种声音,沉默才是病。”
他顿了顿,望向窗外:“后来我发现,那些敢发声的人,活得更久。不是医学上的,是精神上的。他们的痛苦被听见了,灵魂就不至于枯死。”
余惟久久无言。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这些年做的,不过是延续了眼前这位老人未竟的事??让被压抑的声音重见天日。
“我能录下来吗?”他问。
“可以,”周志民说,“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您说。”
“别只放给城里人听。我要你带到矿井、工地、养老院、精神病院……所有没人说话的地方。让他们知道,连一面破墙都能记住声音,何况是人?”
余惟郑重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