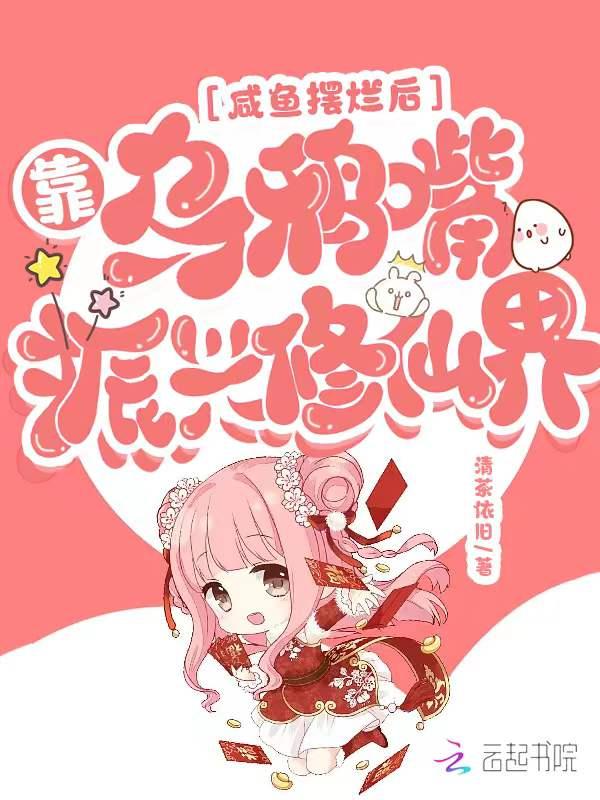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江海共余生 > 第十九章 诊金(第1页)
第十九章 诊金(第1页)
来人是个庄稼汉,肩上还扛着锄头,见刘婶躺在地上气红了眼就要冲过来。聂从犀看了一眼来人,猜测来的是刘婶的夫君,可情况紧急来不及解释,她只能低头继续手上的动作。陆璆自也看到来者,他伸手拦住,问道:“你是刘婶的什么人?刘婶平日里有什么病症,怎突然就晕倒了,若不是我表妹会些医术,今日可麻烦了。”
连环炮似的问句把方大问懵了,他反应了片刻才道:“晓娘又晕了?怎会呢,这毛病许久没犯了。我去找医师!”
“不必找了,我表妹正救着呢,你别靠近,站远些,别给她添乱。”
方大见聂从犀不过是个年轻的小娘子,哪里放心,急道:“你这小子好生奇怪,好端端的拦我做甚,你表妹这样小的年纪懂甚医术,快放开我,我得去寻医师!”
陆璆听了有些不悦,小翁主的医术哪里不好,从上次救田二娘的事能看出,她还是有点本事的。他正欲说些什么,身后的刘婶却已轻哼一声醒了过来。聂从犀按住她,止住她的动作,探了脉发觉暂无危险,这才取下金针,将刘婶的衣衫拢好,冲着陆璆和方大说了声:“好了。”
听到小翁主的话,陆璆这才松开手。方大解开桎梏后忙冲到刘婶身边,小心翼翼的将她扶起来,问道:“晓娘,感觉如何了,可要我去找医师来。”
刘婶因在地上躺了会,嘴唇有些泛紫,她头还有些晕,只轻轻的摇了摇头。方大十分心疼,忙将她拦腰抱进屋里。聂从犀还有些话要交代,也跟着进屋。小翁主既然进去了,陆璆自然不会站在外面。一时间,本就不大的屋子站的是满满当当。
方大小心的将妻子放到床上,在她背后垫了个靠枕,又去端了一碗热茶来慢慢喂她喝下。看着刚刚热情爽朗的刘婶,这时病发变得如此虚弱,聂从犀心里不大好受,她关切道:“刘婶这病应当不是一两日了,平时是不是也常头晕、心悸,容易口干乏力,有时还会腿软耳鸣?”
刘婶眼中一亮,她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以往发病时都是家人连掐带喊,还得灌几碗浓浓得汤药才能缓过来,哪有像今天这样扎几针就好了的先例。她连忙点头道:“娘子说的不错,我这病已有三四年了。有时干完活没觉着多累,可站起来便觉着晕。之前老医师说我这是虚风,开了方子吃,可这病时好时坏,总不能根治。”
聂从犀又摸了摸刘婶的脉,沉吟片刻道:“婶子发病时的症状虽和虚风相近,但却是另一种病。虚风乃是心脾两虚、心肝失氧、舌苔淡红,而婶子的舌苔通红、气阴两虚,上窍无碍,脉象也略有不同,因此当是妊娠虚劳。1若我没有猜错,婶子最小的孩子当有四岁了吧。”
一旁方大不由道:“你怎知我家幺儿四岁?”说着还看向妻子,想知道是不是妻子说的。刘婶更是诧异,她可没提过自家孩子的事。
聂从犀微微一笑,继续解释道:“若胎儿较大,对母体产生压迫,便容易在怀孕时出现这种病症,且极易被认为是孕妇体弱,治错了方向怎能彻底根除病症呢?不过婶子不必担心,只要按方吃药,这病不难治。”
“真是神了,娘子只摸我的脉,居然能将我家幺儿胎大之事都摸出来,实在神医啊。快,老方,快去给神医备纸笔开方。”刘婶这会已经完全缓过来了,听聂从犀将自己的情况说的准准的,敬佩的不得了。方大忙去拿了纸笔来,想起自己刚才那么不客气,很是不好意思的搓着手喃喃道:“实在不知神医小小年岁便能有如此医术,失敬失敬。神医救了我家婆娘,便是我一家的恩人。”说着递过来一个红布包,不用看也知道里面包着几个大钱,“还请神医笑纳,莫要嫌弃。”聂从犀左手执笔,洋洋洒洒写下归脾汤的药方,略一思忖将人参划去改为党参,递给方大,又将红布包推还回去,道:“按此药方先吃五副,然后改一月一副,半年后即可拔除病根。记得此方中酸枣仁需先炒制,否则药效要打折扣的。至于诊金,刘婶早先便付过了,不必多给。”
刘婶愣住:“我何时付了诊金,从你们进门到现在,我不过就端了两碗粗茶……”她反应过来,急道,“不过两碗粗茶,如何能抵救命之恩,神医莫要推辞,午间我家大郎从镇上回来,还需整一桌好酒菜感谢神医。”
听到“镇上”,聂从犀心念一动道:“婶子莫这样称呼,倒是显得外道了。早先我与表兄赶了许久的路,实在口渴难忍,多亏婶子那碗热茶,是刘婶您心有善念才救了自己。诊金就不必了,劳烦方家大哥回来整席面更是不必。”
“嗨,我家大郎在镇上的米铺做工,这几日就要往外面几个县送粮,今天本就该回来的。神医……不,女郎,女郎可别再同我们客气,一定得留下吃盏酒。”方大说起儿子,神色中有掩饰不住得骄傲。聂从犀闻言看了陆璆一眼,陆璆竟读懂了她的意思,接话道:“既如此,诊金的事情便不要再提了,也别再一口一个神医,显得生分。表妹,方叔和刘婶盛情难却,我们不要拂了人家的好意,便留下来安安他们的心,你再替刘婶诊治一番,耽误不了多少时间的。”
聂从犀状做勉为其难的点点头,坐在刘婶边上问她些平日的情况,刘婶是个健谈的,不多会将自己家的事如倒豆子一般都说了出来。若说田二娘是苦命,那刘婶则是好命了。公婆慈和,丈夫恩爱,膝下两儿一女都乖巧孝顺,家中生活也算宽裕。大儿子方厚在镇上最大的米铺做个小管事,女儿和小儿子还小,平日里多由婆婆照顾着。聊了不多会,方大便将药抓了回来,聂从犀称不放心,要亲自去煎药,刘婶夫妇自然是千恩万谢,方大更是要宰只鸡宴客。陆璆跟着到了厨房,抱臂斜靠在门框上,看聂从犀熟练的生火煮药,问道:“你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为何要留在这?”
刘婶是个利落人,家里的柴火堆在高处,一点没有受潮,火一下便升起来了,聂从犀盯着炉子控制着火候,轻声道:“先前刘婶提到镇上,我只是想打听些东垣的消息。可她还说方厚在临记米铺做工,这米铺是常山最大的粮商,方厚既然负责押货出门,定是对各地的消息都有耳闻。我们既然打算扮成流民,总得知道路上的情况,省得又被查的落荒而逃。”
“你想混进商队?”陆璆神色有些怪异。
聂从犀看他一眼,莫名道:“当然不是,你我都算危险人物,若是给商队招来麻烦可怎么办,只是打听消息而已。”
陆璆听到这话松了口气,他也是这样想的,不可为了自己方便而伤及无辜。他点点头表示认可,然后拖过一个小凳子,坐在聂从犀旁边看她熬药。小翁主的手指修长,骨肉均匀,指甲修剪的圆润整齐,泛着健康的粉色光泽,虽然涂了变色的药汁,但仍然可见肌肤细腻柔滑。她一下下的扇着风,控制炉上的火候,在这逼仄的农家厨房居然也生出一分闲适之感。陆璆拿过她手里的扇子替她扇炉子,聂从犀一怔,对他这样积极主动的干活表示不解,陆璆没有错过她眼中的讶异,想起她那天说起扮流民时欲言又止的表情,咬牙道:“我那时是受伤了。现在多亏了神、医、照料才康复如初,煽风点火这样的小事我乐意代劳。”
见他将一番好意说的咬牙切齿,聂从犀偏过头去抿唇笑了一下。陆璆气的大力扇了两下,火苗顺势蹭蹭上冒,聂从犀忙阻止道:“火大了火大了。”然后瞪了他一眼,抢回扇子小心的控制火候,陆璆看着空了的手心,也笑了。随着水逐渐沸腾,一股药香味慢慢充满整个空间,陆璆盯着药罐有些出神,不知道父亲现在身体如何了,小翁主看上去是个医者仁心的,自己是不是不应该欺瞒她?可是事关重大,虽然两人有几分患难交情,可小翁主知道一切后还愿意趟这浑水吗?陆璆自诩平日里是个果断的人,此刻却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不该开口。
“若是……”陆璆纠结了半天,然而话还未出口便被外面的动静给打断了。
“阿母如何了?我这就去请镇上万宝堂的医师!”
“别急别急,你阿母已无碍了,是有个路过的小神医救了你阿母,你是不知道啊,几针下去人就好了。”
“神医?别是什么江湖骗子吧,阿父,我说了多少回了,你们有些什么病痛别耽搁,家里不缺这几个钱……”
这动静不必说,定是方家大郎回来了。陆璆听他说小翁主是江湖骗子,瞪着眼正欲出去理论,聂从犀却用扇子阻了他一下,不急不慢的将熬好的药汁倒进碗里,从容的端出院子道:“方叔,药熬好了,快趁热给婶子喂下去吧。”
方厚本以为是哪个赤脚医师在乡野游窜骗钱的,哪想到是这么个秀丽的小娘子,一时有些结巴住了。直到一脸不耐的陆璆从聂从犀身后走出来,方厚才回过神来。
“大郎在嚷什么,别吓着贺家女郎了,女郎快请屋里坐。”刘婶已觉得完全好了,正想去厨房看着药炉,请贺女郎歇一歇,却听到大儿子在院子里嚷嚷,忙出来制止。贺女郎,也就是聂从犀,笑着将汤药递给刘婶,表示自己并不在意。刘婶一仰头将汤药喝个干净,然后才斥道:“我这身子骨我还能不知道,往常发病哪有这么快就能站起来的时候,我这药还没喝就已经大好了。人家好心救了我,你怎么这样不客气,还不快向贺女郎赔不是。”
方厚被母亲这一通斥责的面红耳赤,低着头冲聂从犀抱拳赔礼,聂从犀侧身避开,表示并不计较,一旁站着的陆璆这才脸色好看些。
“好了好了,大郎知错了,快,这鸡我收拾好了,你帮我来厨下生火,快些整个席面出来。晓娘,你喝了药回屋歇着,贺女郎、王郎君,都歇着、歇着。”方大满脸笑容的招呼着,刘婶见儿子听话,高兴的揽着聂从犀进屋了,嘴里还在念叨:“女郎真是太神了,往日我这病一发作,即便缓过来也是要头晕好几天,心中还常烦躁不安,从未像今日这样,像是没生过病似的。”
“婶子别担心,吃完这些药应当不会再复发了,平日里若是能买到龙眼肉煮些水喝便更好了。”两人有说有笑的进屋,陆璆只好捡了个板凳坐在一旁,想自己的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