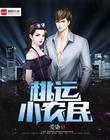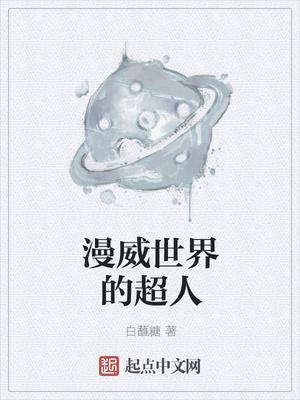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钻狗洞后爱上小奶狗 > 23水毁古籍二(第1页)
23水毁古籍二(第1页)
当天夜里,六人组成的文保小组抵达清溪市檐雨书院。
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10个小时了。
书院外围依旧堆着沙包,前庭地势低洼,地砖缝里仍旧积着没退干的水,踩上去会泛起湿哒哒的回响。
夜雨刚歇,空气中湿气与霉味混合成一种几乎能贴在脸上的味道,让人喘不过气来。
一进门,众人便看到礼厅正中那张展览长桌上堆满了古籍残卷。
纸张卷翘、封皮开裂,有的页面边角已经出现灰白霉斑,墨迹洇开,一页页叠在一起,像是一座被雨水吞没的文献孤岛。
所有的志愿者都穿着文保局统一配发的深灰色风衣式外套,肩膀还带着反光条。
领口与袖口已经微微泛湿,沾着些未干的雨痕。
几位志愿者正在桌边尝试初步的分类,但处理的方式十分混乱,有的按图册尺寸排顺序,有的甚至根据封面颜色堆叠。
一位志愿者正拿着一摞湿漉漉的谱册页,迟迟不敢落手,像生怕一碰便碎。
林序南一眼扫过那些正在徒手翻动残卷的动作,眉心微皱。
不等文保局的工作人员向这些志愿者做个简单的介绍,便快步绕过台侧,从防潮背包中取出湿度与ph检测仪,立刻开始测取当前的环境数据。
仪器发出细小蜂鸣,他抬头扫视上方横梁,对着裴青寂说:“厅内湿度百分之九十六,纸张已超稳定临界,空气ph值偏酸。”
裴青寂站在门边没动,环视一圈后便已了然,他冲着陪同的文保局的工作人员点了下头示意不用介绍尽快开始。
随后,他向前走了几步,在礼厅侧墙一侧空出的位置将书院的地图铺开,用长笔快速标示区块编号,然后转身对着其他人开口:“别动书了,所有文献停止转移。”
语气不高,却稳,语调一落,全场动静立止。
“先从纸质结构和装订工艺判断。”
他走到左首那一堆纸卷前,指尖掠过一页泛潮的封边。
“这批是棉纸加生漆封边,脊线断了但墨层稳定,可以低温环境脱湿。这边是连页毛边本,中页有局部吸附粘连,要立刻控温隔离。”
“——现场总共分六类。”他抬头,目光扫过现场每一双眼睛,“每类编号贴签,搬运路线只走中轴。”
空气立刻静了下来。
滴水声从屋檐上传来,一滴一滴,像在对齐指令的节拍。
林序南起身,将检测数值迅速同步到平台,顺手抽出记号笔,站到裴青寂身侧,毫不犹豫地在图纸边缘添上一栏。
“这里,我加个辅助参数。”林序南的笔尖点在分区表右侧,“标湿度等级,方便二次判断。”
裴青寂低头看了一眼,没多问,只点了点头,“可以。”
两人语气极简,动作连贯,像两个早已对表的齿轮,精准无声地咬合。
原本混乱的现场,开始沉稳地运转。
许南乔默不作声地站到林序南身边,接过仪器操作手册,一页一页地翻到检测流程那页。
他戴着手套,口罩未摘,动作稳准,跟着林序南的节奏将工具整齐分发到各分组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