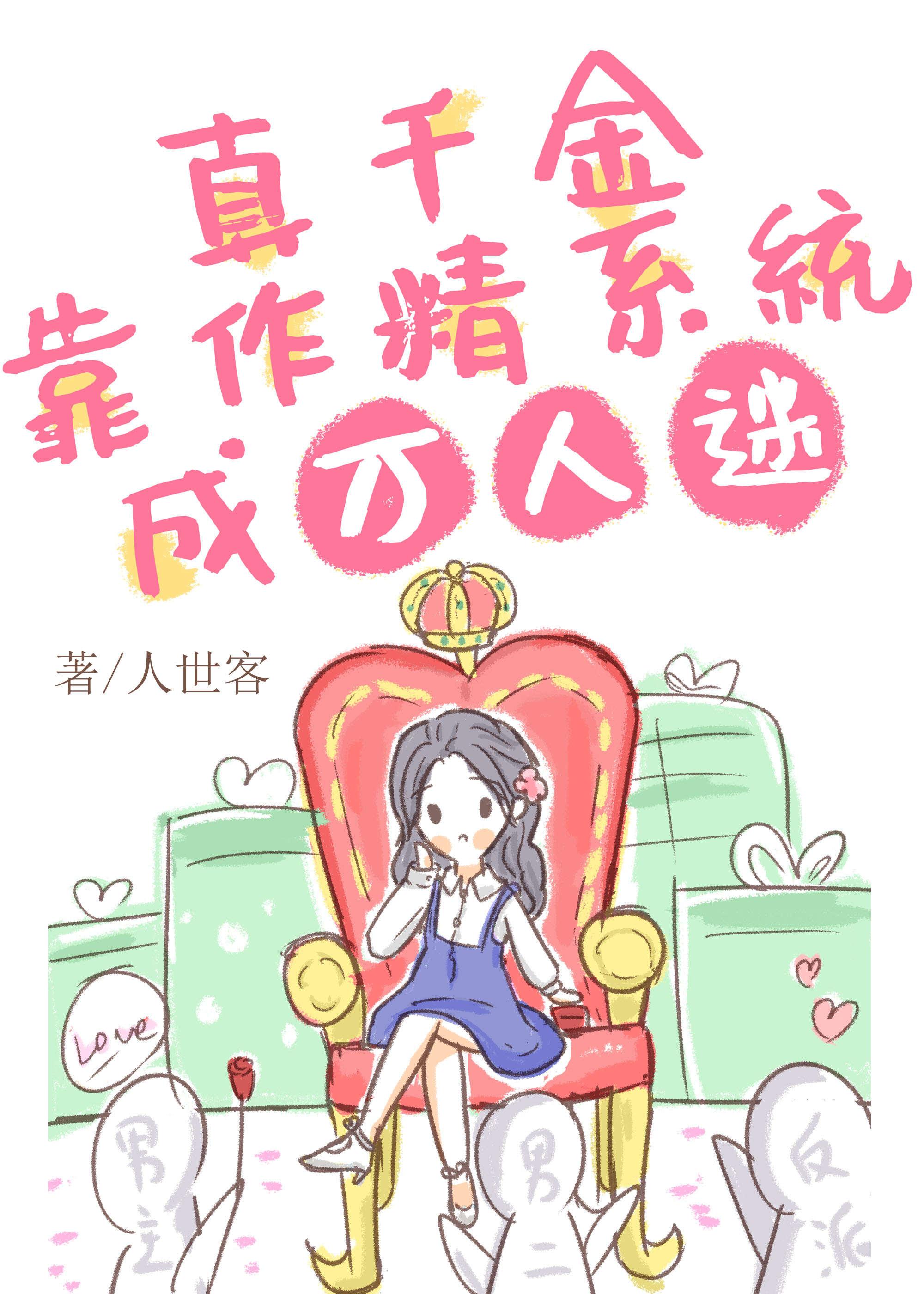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死遁后纨绔竹马黑化了 > 3040(第6页)
3040(第6页)
吴娴刚走进天牢,就险些被飘飘洒洒的纸迷了眼。
她故作被吓到,向一旁侧了侧身,一脚踩在湿滑的青苔上,踉跄两步,鲜艳衣摆蹭到地上的泥渍,一时间很是狼狈。
一旁跟着她的引路宫女见状,花容失色,紧张地小声絮叨:“姑娘,您等下还要面圣,万一被圣上知道您偷来天牢看望这样恐怕不妥。”
吴娴闻言,面容也紧张起来,想要伸手擦掉那团污渍,却被蹭花开,浸入织物纹理更深层。
她看起来比宫女还慌张,用力搓了搓指尖染上的乌黑,“这可……这可如何是好。”
宫女正要安慰她,吴娴先一步灵机一动,很不见外地攥住宫女的手,满眼希冀,“姑姑能否替我取一身衣裳来。”
“当然,姑娘莫慌。”宫女安慰她两句,叮嘱她不要乱走,就撂下人急匆匆去拿新衣裳了。
吴娴好脾气地笑了笑,神情温柔怯懦,目送着宫女远去。
来之前吴娴打点过狱卒,如今天牢内的防守少了一半。
她鬓发已经梳成了很成熟的模样,点翠步摇颤颤,一身喜庆的朱红色衣裙,仪态端庄,面无表情地从两旁癫狂或是平静的牢房走过,无视了疯狂的死囚发出的声音,最终,那双缀着珍珠的鞋停在尽头。
借着微弱的光亮,吴娴朝牢房之中笑了笑。
“沈适忻,好久不见,娴儿今日来,是要向你分享喜事的。”
牢房内一片死寂,吴娴却没有被人漠视的不快,在原地来回踱步,最终一拍手心。
“娴儿将是四皇子的侧妃了,沈哥哥,你瞧起来很意外,是不是好奇,为何我没与我那父亲一同软禁?”
她唇还是微笑的弧度,眼睛却盯着落在栏杆上的小虫,似喟似叹,“他这个当爹的不中用,做女儿的总要亲自争取。”
“四皇子蠢笨,却好拿捏,他那正妃也是个无权无势的。我给他下了蛊,一字一句告诉他,他爱我,爱得离不开我,非要娶我进府才好。”
吴娴拨弄着耳朵上的东珠,微微歪过头,像是不好意思一般。
“于是他在查到吴家前一日来提亲。郎情妾意,娴儿不得不嫁了。”
吴娴一口气说完这么长的话,慢慢蹲下来,华美的裙摆拖了地,她却没有一丝惋惜,任由金银泄地狼藉。
她手指间摩挲着什么,眼神落在暗处的沈适忻身上,杏眸眯起,往日眼波流转的瞳透不进一丝光亮。
“那蛊本来是想趁灯会下给你的,沈适忻。可惜你是个蠢的,偏要一意孤行,与谢璇衣做一对火海鸳鸯。那时我就后悔了,杀鸡焉用牛刀?”
她动作停了停,倏然站起来,轻笑一声,“所以我今日是来和你道别的,顺便……送你一些黄泉路上的小礼物吧。”
吴娴从指尖褪下抚摸着的东西,银光一闪,她捏在眼前打量一瞬,恩赐一般顺着缝隙丢进牢房内。
“喏,抄家那日从你府上搜出来的好玩意,四皇子说新奇,便送给我了,沈适忻,你看看眼不眼熟?”
闪亮的小环在地上弹了两下,没入散落的稻草。
沈适忻靠着墙坐了许久,阖着的眼顿时睁开,脸上才有了除死寂外其余神情。
他颤抖着骨节突出的手指将银色素圈紧紧攥住,却又生怕染了血,不舍得握太紧。
吴娴很满意看到他这幅样子,很新奇地凑过去,丝毫没有先前被血腥气冲得蹙眉的姿态。
“也罢,他到底是要比你先上路了。”
“你说什么。”黑暗中,吴娴听见今日的第一句哑音,堪巧对上沈适忻几乎含血的双眼。
她拧眉,不耐地后退一步,“我说,谢璇衣要死了,陛下想要血洗的何止世家,否则怎会让他去姜城送死。”
有异心的何止世家,当然还有早已各踞根节的北斗领事。
皇帝年迈,疑心极重,否则又怎会急不可耐从沈家下手,又怎会频频将得力下属迁离漩涡中心。
听到远处带着回音的脚步声,吴娴面色微冷,笑容嘲讽地留下一句“珍重”,甩袖快步离去。
沈适忻在稻草干燥的部分反复擦净左手,手背上留下深深浅浅刮伤的红痕,心乱如麻。
他攥住戒指又松开,无比珍视地细细摸过每一寸,眼神落在头顶那一寸窄小的天光。
吴娴说,谢璇衣要死了。
不会的,他怎么会呢,他与旁人不同的。
沈适忻在心底喃喃自语,仿佛要争出所以然,安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