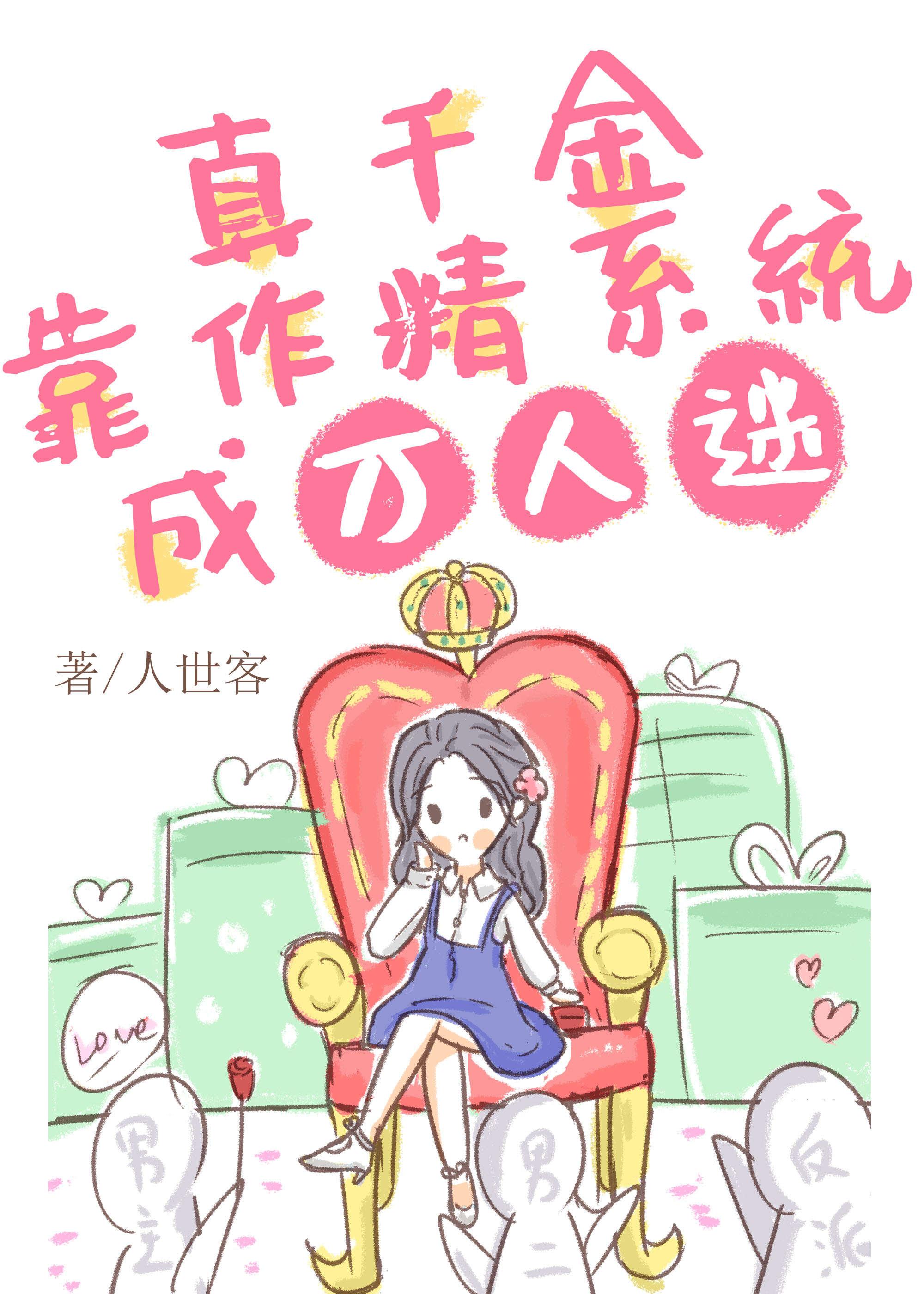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死遁后纨绔竹马黑化了 > 3040(第5页)
3040(第5页)
“你也配提他?”
开阳“哟”了一声,“那你呢,沈大人,你配吗?”
他长吁短叹,千回百转地“哦”了一声,抽出一沓信纸,一张张当着沈适忻的面抖开。
每展开一张,沈适忻脸上的血色就褪去一寸。
开阳把成沓的信纸在他面前晃了晃,假模假样感叹:“倒不知道沈大人如此痴情。”
信纸成色很新,左右超不过一月,可纸面上却已经毛毛躁躁起了褶皱,像是被人摩挲过千千万万遍,墨迹已失去了光泽。
像是被人放在枕边,寄托着某份朝思暮想,情深至切。
字体圆润,像是运笔之人用不惯毛笔,整体却很清秀。
写字之人成熟了太多,却还是有某一部分与从前并无差异。
沈适忻看着,目光有一瞬停驻。
他从北漠回来前,就猜到皇帝要对世家下手。
只是千算万算,算不过吴家为了自保,先一步把他卖了。
而他当时远在北漠,府中下人只能借口他伤痕未愈,闭门不出,也因此错失了扳倒吴家的最后时机。
若说后悔,他倒是不后悔的。
这些都是他欠谢璇衣的,为他受伤,甚至为他流亡、殒命,现在都心甘情愿,如若蜜糖。
可是他也怕,他怕自己真死在这座暗无天日的囚牢里,身边连一丝谢璇衣的讯息也不剩下。
他不想死得太干净,就好像枉费了昔日那番纠缠。
开阳把他这幅怔愣的样子看在眼里,轻笑一声。
那沓信纸被他合拢在手心,微微用力卷了卷,收成一束漂亮的形状。
之后,摊开,撕碎,扬起。
不知道从何处吹来一阵阴冷的风,天牢里的窄小天光倾泻,竟也微微飘起了雪。
那捧飞扬的碎屑就像泛黄的飞雪,掺杂着四处散去,有些落在墙壁上的烛台里,骤然明亮,却又转瞬而逝。
“实在是在下记性不好,忘了,这大概是沈大人留在身边的最后一点慰藉了吧。”
开阳笑得弯起眼,指挥狱卒,“可千万别动沈大人的心头宝呀。”
那群狱卒贯来会见风使舵,点头哈腰地送走了开阳,就对沈适忻冷眼相待,毫不犹豫地清扫走满地纸屑。
“黑黑白白看着怪晦气,也就你还当个宝。”
他们说着,要去夺沈适忻手心攥着的最后一把,却无论怎么用力,都抠不开沈适忻的手心,只得作罢,重重锁死了牢门。
几不可察的雪还在断断续续地落着,沾地就化作一滩冰水,狼藉地润湿了青苔。
沈适忻慢慢松开手。
手心里揉皱着一把淡黄色的宣纸。
他自残伤透的掌心,两个血洞还没愈合,刚刚结痂的创口又被指甲掐破,浅红的液体濡湿了贯会吸水的宣纸。
斑驳狼藉,面目全非。
牢房里干净地方不多,他几乎温柔地将那一把碎屑放置于此,指甲缝里染透了血腥气,颤抖着徒劳地想要拼凑起来。
可是那些纸屑太轻了,不过他一抬手,就尽数掀翻,像一群刚刚破茧的白蝴蝶,头也不回地离他远去。
似乎在嘲笑他,做尽了无用功,不过都是自欺欺人罢了。
他与谢璇衣几乎是朝夕而对的八年,他笑过的每一声,骂过的每一字,此刻都像是最刻薄的诅咒,回馈己身。
沈适忻抬起头,看向那一处天光,却觉得眼前模糊。
大概黄泉路上,他连一盏引路灯都不得见。
第33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