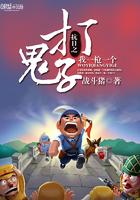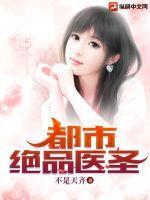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当过明星吗,你就写文娱? > 第二百一十一章 收益更高的打法(第1页)
第二百一十一章 收益更高的打法(第1页)
气氛都到这了,余惟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
抛开直接的好处不谈,在这种大型舞台多演出一次本身就大有裨益,不仅能展示自己,也能抬高自己。
要是真接住了场子,对上是大功一件,对下也是一桩美谈。
。。。
余惟在云南山村小学的屋顶上坐了一整夜。天光微亮时,他听见楼下传来??的脚步声,几个孩子踮着脚从教室后门溜出来,手里捧着粗陶碗,里面盛着刚煮好的玉米糊。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看见他还坐在那儿,惊喜地“呀”了一声,随即又捂住嘴,生怕吵醒了还在睡觉的同学。
“余老师,您一晚上都没睡?”她小声问。
余惟笑了笑,摘下耳机,把录音笔递给她:“我在听你们的声音。”
小女孩好奇地接过,按下播放键。风声、火苗跳跃声、远处山涧流水的回响,还有一段断续的哼唱??那是她昨晚梦里无意识发出的音节,被完整录了下来。
“这是……我?”她睁大眼睛。
“是你们。”余惟说,“整个村子都在这里面了。”
孩子们围上来,争相传听着那段录音,像发现了一件宝藏。有个男孩突然跳起来:“那我们能不能也写一首歌?就叫《屋顶上的早晨》!”
余惟没回答,只是从背包里取出一把迷你口琴,塞进他手里。“试试看。”他说,“声音从来不怕小,怕的是没人愿意听。”
那天上午,他们在操场上用粉笔画出五线谱,拿竹竿当指挥棒,把早读的朗读声编成节奏,把扫帚扫地的沙沙声当作打击乐伴奏。一个患有轻度语言障碍的女孩始终站在角落,双手紧紧绞着衣角。余惟走过去蹲下,与她平视:“你想说什么?不用说出来,用手势、画画,或者……敲一下这根柱子都行。”
女孩迟疑片刻,抬起手,在水泥柱上轻轻叩了三下。
笃、笃、笃。
余惟闭上眼,耳朵贴近柱子。震动传入耳膜,像某种古老密码。他忽然起身,翻出吉他,以那三声为动机,即兴弹出一段旋律。孩子们瞬间安静下来??那调子低缓而温柔,仿佛月光落在干涸的井底。
“这就是你的歌。”他对女孩说。
她怔住了,眼泪无声滑落。
中午,村长带来消息:县教育局听说这里的孩子在“做音乐”,派了位教研员明天要来考察。话音未落,几个家长已皱起眉头。
“搞这些虚的有啥用?”一位父亲抱着柴禾进门,“娃连英语都学不会,还唱歌?”
余惟没有争辩。傍晚,他邀请所有村民参加一场“无声音乐会”??每人发一张纸、一支笔,写下最近一次让自己心头一颤的声音:有人写“孩子发烧时的第一声哭”,有人写“老牛临死前最后一次反刍的声响”,还有人写“媳妇出嫁那天踩碎门槛的咔嚓声”。
然后,余惟把这些文字贴在教室墙上,逐字诵读,并将它们谱成一段纯器乐曲,用口琴、空瓶、铁皮桶和木尺演奏出来。
当最后一个音符消散在晚风中,那位曾反对的父亲默默走到墙边,撕下自己写的那张纸,又重新写了一遍,递给余惟:“加进去吧,这次我想让闺女听见。”
第二天教研员到来时,看到的不是排练整齐的合唱,而是一群孩子正围着一台旧收音机,试图把昨夜录制的曲子转成磁带。他们笨拙地接线、调试,脸上沾满灰尘,眼神却亮得惊人。
“这不是教学成果展示。”教研员沉默良久才开口,“这是生命在主动发声。”
他回去后提交了一份前所未有的报告:建议将“声音叙事工作坊”纳入乡村美育试点课程,并申请专项资金支持。半年后,全国首批二十个“声音种子计划”实验校挂牌成立,云南这个只有三十七名学生的山村小学位列其中。
而余惟,早已踏上新的旅程。
这一次,他南下广州,走进一座昼夜运转的电子厂。车间里五百条流水线同时作业,机械臂精准舞动,工人们戴着耳塞,面无表情地重复同一个动作。厂方负责人起初极不情愿:“我们这儿没故事,只有KPI。”
余惟没反驳,只提出一个请求:允许他在午休时间,借用员工活动室十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