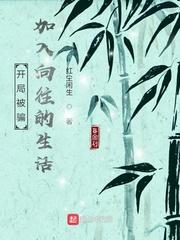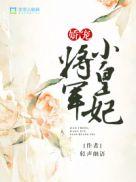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贫道要考大学 > 第173章 以后每天都这样一起回家啦(第3页)
第173章 以后每天都这样一起回家啦(第3页)
>和所有被误解的沉默
>愿后来者,终得言说
碑前摆着几束野菊,还有几张叠成心形的纸条。那是村民们自发写下的寄语:
“爸,今年清明我没烧那么多纸钱了,我给您录了一段话,说了很多小时候的事。”
“老公,孩子考上大学了。我没告诉你,是怕你在那边担心。其实我也很想你。”
“我不知道你是谁,但谢谢你听我说完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我现在已经开始学画画了。”
这块碑没有登记在任何民政名录中,却被当地人称为“心碑”。每逢初一十五,总有人前来献花、留言,甚至只是静静坐着。
某日傍晚,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拄拐而来,在碑前坐了整整两个小时。临走时留下一封信,托温知夏转交。
信中写道:
>我是当年那个举报你们“传播迷信”的记者的母亲。三年前我儿子患抑郁症自尽,遗书里有一句:“这个世界太吵了,没人愿意安静地听我说话。”
>
>后来我找到了他电脑里的加密文件夹,全是你们平台的语音回放记录。原来他曾匿名倾诉过,而每一次,都有人认真回应。
>
>那时我才明白,他不是不想活,他是太想被人听见。
>
>对不起,我曾经误解了你们。请替我向所有还在黑暗中说话的人转达:
>“我在这里,我在听。”
温知夏读完,久久不能言语。她走到药房深处,取出珍藏多年的紫苏膏??那是师父留给她的唯一遗物,据说能安神定魄。她刮下一小块,混入艾草灰,亲手制成一支安魂香,在“心碑”前点燃。
青烟袅袅升起,融入山雾之中。
谷雨那天,陈拾安收到一封特殊邀请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青年发展委员会希望将“回声计划”列为“全球社区心理健康创新典范”,并在巴黎举办专题展览。
随函附有一段视频,来自非洲卢旺达的一所乡村学校。孩子们围坐在太阳能录音设备前,轮流对着麦克风说话。有的说想念战乱中失散的兄弟,有的说害怕夜晚听到枪声的幻觉。当地教师用简单翻译软件接入“青囊云”多语种模块,获得即时支持建议。
视频最后,一个小女孩仰头问道:“老师,如果我们说的话飘到天上,真的会变成星星吗?”
老师笑着点头:“会的。每一颗星星,都是地球上的一个回声。”
陈拾安把这段话抄在笔记本扉页,下面写下一行字:
**“所谓文明,不过是一群人终于学会蹲下来,听另一个人喘气的声音。”**
立夏前夕,卫生室门前的铜铃突然断了一根系绳,在风中摇晃欲坠。赵岩想拆下来修理,却被温知夏拦住。
“别动它。”她说,“让它挂着吧。哪怕只剩半截,只要风一吹,还能响,就说明还有人需要它。”
当晚,陈拾安做了个梦。他梦见自己变成一棵大树,根须深入地下,连接万千脉络。每一条都通向某个正在说话的灵魂??城市地铁站里低声啜泣的白领,边境哨所中思念家乡的士兵,重症病房内攥着亲人手的老人……
他们的声音汇成溪流,顺着树干向上奔涌,最终化作枝叶间的沙沙作响。
醒来时,东方既白。
他推开窗,晨光洒落肩头。远处田野已有农人劳作的身影,近处,一只麻雀落在铜铃上,歪头看了看他,振翅飞去。
铃铛轻晃,发出清越一声:
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