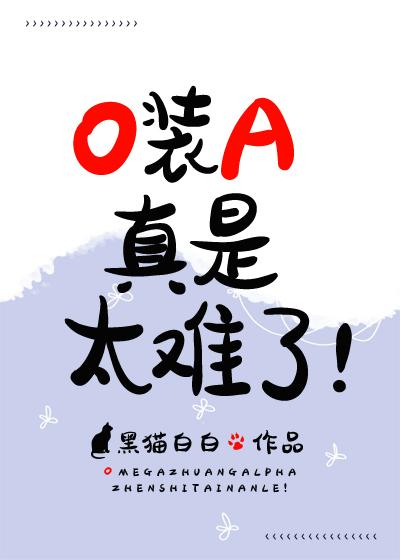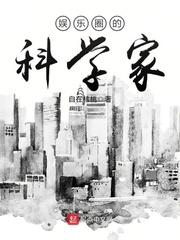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贫道要考大学 > 第173章 以后每天都这样一起回家啦(第2页)
第173章 以后每天都这样一起回家啦(第2页)
与此同时,一场风暴正在酝酿。
二月底,《财经前沿》刊发深度报道《谁在瓜分青少年情绪数据?》,直指“梦语计划”存在“变相采集隐私”“诱导未成年人暴露心理弱点”之嫌。文章引用匿名专家观点,称此类平台“打着公益旗号,实则构建新型行为监控网络”,并配图一张经过模糊处理的后台界面截图,标注“疑似用户脑波分析模型”。
舆论迅速发酵。微博热搜挂出#警惕心灵鸡汤变精神控制#,评论区两极分化。支持者痛斥媒体“蹭流量抹黑善举”,反对者则质疑:“道士治心病?这不是迷信是什么!”
压力很快传导至官方层面。教育部紧急约谈项目组,要求暂停新增试点,全面接受第三方伦理审查。
那天下着冷雨,陈拾安独自坐在会议室,面对七位评审委员。有人质问他为何用“道士”身份开展心理服务,是否涉嫌传播封建迷信。
他没有辩解,只是打开投影,播放了一段视频。
画面中,是一位藏族老阿妈在帐篷里对着手机说话:“格桑啦,我知道你在天上看着我。今年牧场上的花开了,牛也下了崽……我想你,但我不会再烧香求你回来了。我会好好活着,替你也活一份。”
语音结束后,系统生成一段文字回应,以藏文显示:“你说的话,风会带给她。你流的眼泪,大地会替她接住。你们之间的爱,从未断绝。”
老阿妈看完,双手合十,轻声说了句“扎西德勒”。
“我们用的是现代技术,但疗愈的本质从未改变。”陈拾安说,“无论是诵经、祷告,还是心理咨询,都是人类试图与痛苦对话的方式。我只是换了一种语言罢了。”
评审团沉默良久。最终,专家组出具报告:
**“该项目无证据表明存在数据滥用或精神操控行为,其核心理念符合积极心理学发展方向,建议继续推进,同时加强公众沟通与透明度建设。”**
风波暂息,但陈拾安清楚,真正的挑战才刚开始。
三月初,他受邀参加全国心理健康教育研讨会。会上,一位知名精神科教授提出质疑:“你们强调不诊断、不干预,可如果发现严重心理危机,难道也不采取医学手段?”
“当然要。”陈拾安答,“但我们坚持‘第一响应者非医疗化’原则。就像感冒不会立刻动用抗生素,大多数情绪困境也需要先经历‘自然愈合过程’。我们的角色,是提供一个安全容器,让人敢于袒露伤口,而不是急于缝合。”
他举例说明:一名高三男生连续两周上传录音,内容全是空白噪音。系统识别出异常后,触发黄色预警,由志愿倾听员主动联系。起初男孩拒绝沟通,直到某天凌晨三点,他终于开口:“我怕睡着,一闭眼就梦见坠楼。”
倾听员没有劝他“别胡思乱想”,而是陪他数呼吸,讲自己小时候怕黑的经历,甚至一起听窗外的虫鸣。“你知道吗?最黑的夜里,蟋蟀叫得最响亮。”
三天后,男孩主动预约线下心理咨询,并开始服用医生开具的短期抗焦虑药物。
“技术和人文,从来不是对立面。”陈拾安总结道,“AI可以识别危机信号,但治愈的力量,永远来自人与人之间的温度。”
会议间隙,他在茶歇区遇见一位穿灰呢大衣的老者。对方递来名片:周明远,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退休研究员。
“小陈啊,”老人握着他手,眼里有光,“我看了你那封公开信,整整三十年了,终于有人说出这句话??‘你不需要坚强,你只需要存在’。”
他顿了顿,声音微颤:“我女儿就是自杀离世的。那时候没人教她可以哭,没人告诉她累了就能歇。她留下的日记里写着:‘我不想成为负担,所以我消失了。’”
陈拾安喉头一紧。
“你们做的事,”老人拍了拍他肩膀,“是在给千万个家庭重新点亮一盏灯。”
春分前后,项目迎来新突破。国家卫健委正式将“青少年情绪健康筛查”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包,明确鼓励运用数字化工具开展早期预防。首批专项资金拨付到位,“回声计划”将扩展至二十省一百县。
更令人振奋的是,高考改革调研组派人来访,探讨是否可在语文作文题中引入“心灵书写”模块??不限主题,不设评分标准,仅作心理评估参考,且完全自愿提交。
“这意味着,”李处长私下透露,“未来高考不仅是选拔机制,也可能成为一次大规模心理关怀行动。”
消息传回村里,赵岩兴奋地组织孩子们排练情景剧《耳朵的故事》。舞台上,一个小男孩扮演过去的自己:“妈妈说我爱哭,就把我的眼泪存进玻璃瓶,说攒够一百滴就能变成勇士。”另一个孩子扮演现在的他:“现在我知道了,我不是要用眼泪换勋章,我是要用它们浇灌心里的花。”
演出结束时,台下掌声雷动。温知夏悄悄抹了眼角,回头看见陈拾安正望着她笑。
“怎么?”她问。
“我在想,”他说,“也许有一天,每个考场外都不再挤满祈福的香火,而是响起轻柔的音乐,播放一段引导冥想的音频。让所有少年进场前,都能先听见自己的心跳。”
她点头:“那样的考试,才算真正公平。”
清明时节,细雨如织。他们在村后山坡上立了一块无名碑,上面刻着三行小字:
>这里埋葬着未曾说出口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