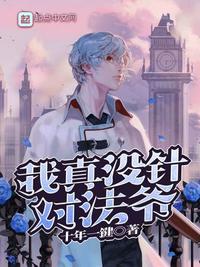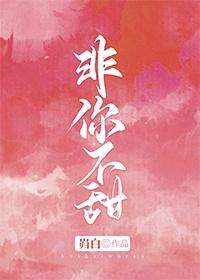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大明:哥,和尚没前途,咱造反吧 > 第一千二百一十七章 人不知责归何处(第1页)
第一千二百一十七章 人不知责归何处(第1页)
朱标不抬头:“按旧规。”林奉道一愣:“可东市先例……”朱标终于开口,淡淡一句:“此非东市,此为你林奉道之案。”“既为你案,自依你策。若你无定策,不必来问我。”林奉道面色一变,躬身应下,却心下惴惴。待他退出后,顾清萍缓步入内:“您是在立规?”朱标将手中册子合上:“不是立规,是立胆。”“我若事事断之,他们便事事问之;我若退一步,他们便需前进一步。”“外策堂已散,是我让他们散的,我便该逼他们——不问我,而问自己。”顾清萍凝视他片刻,忽而轻声一叹:“您这法子,是在逼人长出骨头。”朱标转过头,看她一眼,神情未变:“若无骨,岂能撑国?”然而,朝中远未平静。礼部尚书张衡之在翰林院私议中直言:“太子性多疑,好立异格,不通旧情。”是日夜中,朱标独坐于建德堂中,未设灯烛,堂内唯月光一线映于卷案之上。顾清萍端来一盏姜茶,他却未伸手。“我若不能让他们认我,不是凭声望,而是凭章法。”“张衡之有其旧门生三十余人散于六部八司,我若不破此枝节,何以见我心?”顾清萍沉声道:“那您要动他?”朱标摇头:“不。我要让他动我。”数日后,朱标下令:设“案后评议制”。凡东宫处理之案,结后三日,六司之中自推三人评其成效,以示自律互监。首案即南市误册之案。而推举评议者之一,正是张衡之门下陈庭礼。案评次日,陈庭礼于评文中言:“太子不预调审,责在官吏,虽非失政,然亦失于慎。”并于末注:“若设主审官则免此偏。”此言一出,朝中震动。此人虽未名诋太子,却已实陈太子失察之处。众人屏息,只等朱标回文。建德堂内,顾清萍望着那道呈上之评,低声问:“您如何回?”朱标提笔,只书三字:“言之是。”随即另纸手书一道:“即日起设东宫‘辅案使’,不专责批,唯列疑议,遇有政案未决,得署‘存问’,交吏部录入案尾。”“首任辅案使:陈庭礼。”顾清萍一愣,复而轻声笑道:“您果然……敢于用人。”朱标收笔,道:“若我连一封议我之书都不能接,我怎配听天下人言?”“陈庭礼能斥我一次,便能斥我十次。”“我就要他斥我——斥得有理,斥得有法,斥得我都不得不改。”三日后,御书房。朱元璋批阅《辅案录》初册,眼神沉静。程守义低声问:“陛下……太子此举,不惧反噬?”朱元璋笑了笑,摇头:“不怕。”“朱标这孩子,如今已懂得用人,不问忠否,只看能否。”“他知我弃宠纳谏,也懂,得人心非靠仁慈,而靠服气。”“这一步——走得有胆,也有度。”“他终于,真坐稳那把交椅了。”王府书房。朱瀚望着案上的辅案录末页,轻声道:“东宫,如今已不需我设局了。”“朱标已会自设风口,自撑风骨。”“我只需站在风后,等他真能顶得住——风起时的那声‘孤’字。”黄祁低声道:“可这天下风还未起。”朱瀚收起书卷,抬眼望天,笑了:“不急。”初夏渐临,京中暑气尚未浮起,宫中已是烛影摇红。建德堂内,朱标独坐一隅。却有一处极淡的朱批,字意含糊,几不可察:“数目有疑,当问所在。”这五字,出自吏部外曹徐谨之手,本属随批,但被左司陈庭礼于“辅案录”中擢出。卷上朱标加批:“录之,延问。”三日后,“辅案堂”首开质疑席。朱标不设主座,不设堂审,仅遣吏部、户部、东宫三方人等八人入席,共议此“疑数”是否为故失。那页数字是南直隶元月折收银两数目中,有一地数额平空多出三百两。未久,蒋希远入场,其人面色沉静,躬身一礼:“殿下,此误不由属下,乃南郊郡录簿册错传,实为‘统账未删’,后页已勘明。”陈庭礼却不应,只取出副册,道:“蒋典事,阁下三月前曾言:‘折统若误,当存单日录’。然此事并无单日之迹,何以言‘错传’?”蒋希远缓声道:“当日南郊火患,存单被焚。”陈庭礼冷然一笑:“那便是‘说了便是’?”朱标始终不语,只将案中朱笔倒置,手指轻敲桌面。蒋希远语气不改:“若无证,我愿受责。”陈庭礼却忽而抬头:“责在何处?东宫未设罚名,太子未书戒条。您愿受责,便是谁都无权问您何责。”一句话,静若雷声。堂中忽而无人发言。良久,朱标开口:“陈庭礼。”,!“在。”“你这句话,说得极好。”“本朝虽设吏典、设使辅,然典使不过法下书人,非律下之官。”“若太子设局、设言、设法,却不能明其责名、刑条——便是东宫设政之懒政。”“我错,不在蒋典事,也不在南郊录账。”“在我。”“我用人之法不周,责成未明,便该以我身,为首责。”众人骇然,陈庭礼眼中亦闪过惊色。朱标却抬笔,于案上亲书一道:“东宫太子,责未立法,误使典使,罚停外政七日,不列册、不断案。”“由顾清萍摄案三堂,七日内太子不得主议。”顾清萍自后堂疾步入前,拦身便道:“不可!”朱标却摇头:“清萍,你知我所思。”“今日若不立责,明日设十堂百案,皆成虚空。”“我行政,是为正政,不是为显我朱标。”她久久不语,终于拱手低头:“妾遵命。”而此事,三日之内,传遍六部。户部侍郎私议:“此举虽显公正,却自降权势。”吏部中允则曰:“太子敢责己,胜于责人百倍。”朱元璋听闻此事,仅笑而不语,写下一句:“太子已可独承其局。”第六日,王府。朱瀚翻阅录简,笑问:“七日,不短。”黄祁道:“朝中褒贬不一,有人赞东宫自省,有人疑其为避锋。”朱瀚冷哼一声:“避锋?这叫领锋。”“朱标用自责,逼群臣问己。”“他不裁,是让你们自己裁;他不议,是逼你们自议。”“七日之后,他若再登案,众人反而不敢妄动。”黄祁道:“王爷要去东宫看看?”朱瀚摇头:“不急。我等他最后一日。”建德堂第七日,天光微曦,朱标独自站于庭前。顾清萍立于阶下:“外间传言已起,有言殿下借自责回避吏议,有言殿下设局避责于他人。”“可昨日外策录中,有九人投文言‘太子行己有节,可为吾主’。”朱标望天而笑:“这才是我要的。”“信我者,不因我讲法而信;疑我者,不因我设责而明。”“东宫不能靠我独撑,而要靠百人之目、千人之言——来撑我。”他缓缓转身:“我退一步,他们才知该往哪走。”而朱元璋坐于御案之后,看着程守义奉上太子之《退堂日录》,翻到最后页时,忽而停住。“怎么这几字,非太子亲笔?”程守义低头:“陛下慧眼,那是……顾贤妃亲代之笔。”“太子罢政七日,未亲笔一句,只于首日批示‘罚名’。”“七日间,顾贤妃代理、众臣自行、外策录满二卷。”朱元璋忽而仰头笑出声来:“好,好得很。”“朱标你这七日未言半字,却让天下知你何为太子。”“你这东宫——真立起来了。”他却又缓缓收敛笑意,低声自语一句:“可你那位皇叔,还不肯来见你。”王府,夜半。朱瀚坐于庭中,不设灯、不设席,只对一壶酒,一盘青梅。黄祁立于侧,忽道:“王爷,东宫来人了。”朱瀚不动,只抬手示意:“让他入。”脚步声至,一人入庭,黑衣未披甲,腰间却有旧佩。来者竟是昔日朱瀚府中暗司旧部,名吴戎。朱瀚淡淡看他一眼:“你不是守北营?”吴戎一揖到底:“王爷,太子有言——请您回堂,设一‘旧人事议’,欲以王爷名义,校录旧部、调修密院。”朱瀚静默良久,终于笑了。“他七日不言,如今第一句话,是请我掌暗局。”“这是告诉我——他已立明堂,想立暗堂了。”吴戎低头不语。朱瀚放下酒杯,起身:“传话朱标。”“东宫暗线,归他。”“但朱瀚这把伞,从今日起,不再遮风挡雨。”“若风再起,就让他自己撑伞。”“我要看看——他撑得住撑不住。”初五未明,太子东宫内院,灯火通明。朱标立于堂前,手中捧着的是新呈《民议折简》百页,由文选司从各处采风所编,字字句句皆来自城中各类百姓、士人、郡生、旧吏之口。顾清萍披衣而至,轻声:“昨夜未歇?”朱标摇头,翻开一页,低声念道:“‘太子设外策之堂,不过饰贤之形,所言不听,所问不改,吾等言官空有唇舌。’——此为翰林院陆监生之语。”“‘折统新法,扰我三月户籍,邻甲未通、民苦调编,何来安政?’——此为平江郡丁户之语。”他缓缓放下卷轴,眉头紧皱。“这是我太子之政,于堂前得声,于民中却得怨。”顾清萍静默片刻,轻声道:“可这不正是设外策之意?”“让真正的声音传上来——不管好听不好听。”朱标苦笑:“是我错了,我以为自己可以站在堂中听百官议,却忘了,百官之外,还有千万人。”,!“我若只问‘政’,不问‘人’,不过又造一个冷法的王朝。”他抬眸,神情清明而坚毅:“我要亲自下街。”顾清萍一惊:“殿下不可——”朱标却截然一语:“不可才要为。”“我设局设堂,是让百官言我之政;但我若不亲行其政,便永远只听得朝语,而听不得民声。”“我要知道,他们到底怕什么、怨什么、痛什么。”她看着他半晌,终于轻轻点头:“那我替您换衣。”申时末,太子换常布素袍,着长衫而出,只带一人——林致远。马车不走主路,自东城北巷穿行入平江坊,再由西柳巷绕至南市旧营。林致远挑起车帘一角,低声道:“殿下可知,此行……只要一人认出,便有万言可毁。”朱标不语,只轻轻叹息一句:“若我太子之位,只靠帘内不破,那便早该碎了。”车停南市口,他缓步下车。街道泥地未干,摊贩林立,一小儿跌于泥中嚎哭,老妇怒喝着前头一名吏员:“你这编录的!我孙儿才五岁,也要入户册?”吏员不耐,冷声道:“折统新制,丁口一户一算,不看岁数,只问人数。”老妇伏地哀嚎:“我儿亡于疫,我孙未成丁,哪来三人税目?!”吏员皱眉欲斥,一只手却忽然伸来,将老妇扶起,言语温柔:“婆婆莫急,若孙尚不足八岁,可呈实户册,请议免丁。”老妇抬头,望见那人眉目清正,衣着却非官袍,怔怔问道:“你是……谁家书吏?”朱标低声一笑:“是平江坊的听政人。”老妇不解:“听政人?”朱标点头:“不入官,不设判,只听你们怎么活,怎么难。”吏员惊觉失言,连忙作揖:“这位公子——”朱标挥手:“你守职有法,责不在你。折统若未明免条,是我东宫未传明令。”“我受教。”他缓缓取出随身携卷,在一角写下:“丁下未满八岁,免纳折统,列补户旁批注。”林致远侧目,看着他写下的字,神色微动。“你真是……在这里写法?”朱标轻声:“若此地无声,那我所写的法,不过是空文。”他走入市中,问茶摊、访菜商、坐布庄、至木行,凡三日之内,不曾宣一名、不发一帖,只做一事——听。“账未清。”“册太繁。”“冬粮少。”“旧法易,新法难。”“人不知责归何处。”朱标每闻一句,便记一句。:()大明:哥,和尚没前途,咱造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