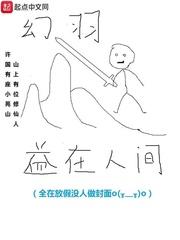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广夏:云涌篇 > 100110(第9页)
100110(第9页)
韦先生这么卖力夸赞长孙青璟,总令她感觉心慌不已。这老头或许真如传闻中所言,觉得背后潜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韦先生……”她有些战战兢兢,不敢接受这份勉为其难的夸赞。
“梵娘,用烈酒擦一下手,把银针也煮一下。”韦先生望着窗口道,“烈酒、葱白水——梵娘就照我平日教你的,把伤口再清理一下,记得千万不要沾染浊气!”
屋外狂风乱作,长孙青璟匆匆跑到窗边,窗外树影狰狞,丫杈有一种奇怪的反光,好像有人吊在那上面摇晃。
她没有惊叫,只觉得自己精疲力竭,眼中出现了幻象,便匆匆阖上窗户。
“梵娘,快到连枝灯边上,再灼烧一下银针,将桑皮线穿好。”
段志玄听得头皮一紧,舌头因曼陀罗酒开始发挥效力而有点迟钝:“老匹夫,你给我好好缝!不然……”
“不然你待怎样?杀了老夫不成?”韦先生用夸张的语气嘲弄这个任侠使气又狂妄自大的年轻人。
“快闭嘴!”长孙青璟恨不得用破棉絮堵住段志玄的嘴。
“高孝璟,你也拿烈酒擦手。”韦先生望着窗外树影,神色一凛,“梵娘,把针线给高孝璟——你给他缝合伤口!”
“什么!”三个年轻人全都不可置信地惊叫起来。
韦先生冷笑道:“我老眼昏花,从不在夜晚替病人缝针;梵娘虽说是个精细的女孩子,但是遇到这种流血开裂的场景能手持烛台不晕厥我就谢天谢地了;高孝璟是个胆大妄为的书生,况且勉强能为自己缝补衣服——我们三个里只能选他了。”
长孙青璟觉得这老头虽然插科打诨,但说得确实也无法反驳便硬着头皮、故作镇定道:“好!”
段志玄发出一阵惨叫:“高孝璟,你上次给自己补衣服是什么时候?”
“三年前——”长孙青璟对段志玄怀疑她做不好针线活这件事有些气愤,但是把自己给小婴儿缝制衣物一事说出来又唯恐遭到韦先生怀疑和耻笑,便故意吓唬他,“外出狩猎时,树枝刮坏了襕袍,没有侍婢在侧,我就自己缝上了。”
“那你缝结实没有?”
“当然!”
“也罢,还是你手稳。等我先念几声观音你再下手。”段志玄给将要动针的和将被动针的两人都鼓了一下劲。
“那你多念几遍。”长孙青璟抬头看看那并不存在的“观音”,又低头向段志玄眨眼,故作镇定地笑道。
“高公子爽快人。”韦先生叹道,“梵娘持烛台,我来教孝璟如何缝补皮肉。——段志玄,你尽管放心,高公子在林子里想出安置梵娘的主意,已经救过你一命了,断不会对你不闻不问,定会救人救彻。”
“不错。”长孙青璟壮胆附和,从李梵娘手中接过了银针。
“高孝璟你不要磨磨蹭蹭,我此时看到观音菩萨正飘在房梁上——真的看到了。”段志玄开始神昏谵语,“你快缝好,等她走了再缝,我非痛死不可。”
“行了,我们知道曼陀罗酒对你有用了。”韦先生上前按住段志玄,“下针、打结时还是会疼痛不止,我找块绢布堵……”
“不准堵我嘴。”段志玄用含混不清的声音抗议道,“我明明受得住,老匹夫又想出些恶毒的馊主意羞辱我!”
“那你自己把舌头咬掉吧。”韦先生不再与他啰嗦,“高公子,从伤口下侧左边进针,刺出右侧——”
长孙青璟强抑住颤抖、晕厥的不适反应,照着韦先生手指在伤口上方空气中划出的痕迹,以银针在段志玄伤口一端穿刺。
“你不要看段志玄的脸,他自己逞强自己忍着——好,右线绕左线两圈拉紧——拉得太紧了,手不要抖!”
长孙青璟额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段志玄忍痛时狰狞的面容使得她明白自己的医术有多么糟糕!
李梵娘一手持烛台,一手为她擦拭汗珠。
韦先生有些焦灼地望了一下窗外:“好,就是这个力道,右线反方向绕左线一圈,再打结——就这样替他缝好。不要疑神疑鬼,他不乱喊你就大胆缝合!你是把行医的好手。”
“志玄你痛不痛?”长孙青璟准备下第二针。
“忍得住。”段志玄咬牙战栗道,“菩萨在我头上悬着呢,她跟我说高孝璟靠得住!”
“你替我谢谢她对我青眼有加。”
“高公子你就这样一针一针往上缝,针脚密一些。梵娘你把灯掌好,不要看别处,特别是窗口树影,半夜里经风一吹就是这个样子,没什么好看的。两个人手都稳一些,段志玄忍住不要发抖时就按住他,省得扎错地方。我去找黄芩蜂蜜膏,听到任何响动你们都不用理睬。”他脸上似乎露出一个若有似无的微笑,“我小看他了。这小子是个当将军的料。”
虽说是去找黄芩蜂蜜膏,可长孙青璟的余光分明瞥见韦先生提刀离开茅屋。
她顾不得想那么多,屏息凝神继续向上缝合,终于将伤口逐渐收拢。
“志玄,志玄!”她望着因疼痛而面部扭曲的段志玄,“如果你疼得受不了……”
“没事,菩萨还在梁上保佑我。”
“最后两个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