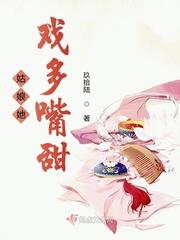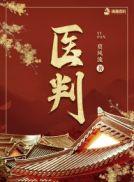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碎凤 > 沉璧(第1页)
沉璧(第1页)
次日的椒房宫请安,依旧是一派庄重雍容的景象。
炭火烧得暖融,驱散了初冬清晨的寒意,我端坐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目光平静地掠过殿内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最终,落在了那个正跪在殿中央、向凤座上的盛望舒行大礼的陌生身影上。
这便是那位新入宫的嘉贵人,金沉璧了。
今日初次正式拜见中宫,她穿着一身浅粉色的宫装,颜色选得谨慎。料子虽是上好的江南织锦,款式却是宫中最常见的,算不得出挑。
我一向以为,北境的女儿都是慕容舜华那般刚烈或是英姿飒爽的。金沉璧倒是不同,身姿纤细,略显单薄,带着一种初来乍到者特有的、生怕行差踏错的紧绷与小心翼翼。
皇后依着惯例,温言抚慰了几句,声音平和悦耳,说的无非是“六宫和睦,谨守宫规,尽心侍奉”一类的场面话。
金沉璧垂首恭听,声音轻柔得如同蚊蚋,带着些许不易察觉的异族口音:“嫔妾谨记皇后娘娘教诲,定当恪守宫规,安分守己。”
待她起身,转向我们这些妃嫔一一见礼时,那份强自撑起的镇定下掩藏的脆弱与不安,便更为明显了。
她依次向端坐上首的慕容舜华、向我、向纯嫔兰殊等人屈膝行礼,每一次低头都带着一种如履薄冰的审慎。
轮到我时,她依礼福身,声音依旧轻柔:“嫔妾金氏,给娴妃娘娘请安。”
我微微颔首,目光在她低垂的眉眼间停留了一瞬,语气温和,却保持着应有的距离:“嘉贵人不必多礼。初入宫中,若有不适之处,可随时告知内务府。”
我的话中规中矩,既未过分热络,也未显得冷漠,如同这宫中大多数初见时的寒暄。
她低声应是,姿态愈发恭顺。
轮到纯嫔兰殊时,兰殊看着她,清冷的眉眼间竟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柔和,并未像其他人那般只是淡淡受礼,反而轻声开口,打破了殿内略显凝滞的气氛:
“嘉贵人这名字,‘静影沉璧,浮光跃金’。范希文公的词意,用在妹妹身上,倒是别有一番清雅幽静的韵味,令人见之忘俗。”
兰殊的语气满是独属于文人的真诚和欣赏,顿了顿,略带一丝好奇道,“只是这名字,不似北地风光辽阔苍茫,倒更像是我们江南水乡里,荡舟采莲时,映着月光走出来的姑娘。”
金沉璧闻言,立刻微微屈膝,姿态放得更低,声音依旧轻柔,却比先前清晰稳定了几分,“回纯嫔娘娘的话,娘娘博学,这名字确是取自汉家典故。”
她顿了顿,长长的睫毛如同蝶翼般垂下,在白皙的脸颊上投下淡淡的阴影,恰到好处地掩去了眸中一闪而过的复杂情绪,“是臣妾临入宫前,特意请族中通晓汉学的长者改的。”
她抬起眼,目光温顺地看向兰殊,又似无意地扫过凤座方向,“既入天朝,沐浴皇恩,便想着一切都该依从天朝的规矩和喜好,方能不负圣恩。”
特意改的。
我看着她那低眉顺眼、近乎完美的恭顺模样,昨日心中那份物伤其类的怜惜与悲凉,再次不受控制地翻涌上来。
为了生存,连与生俱来的名字都可以舍弃,又该是一种怎样的无奈与决绝?
我正暗自感慨,却见金沉璧在应对完兰殊后,目光悄悄投向了左上首姿容明艳、即便安静坐着也难掩周身张扬气场的慕容舜华。
慕容舜华向来不耐烦这些繁琐的礼节,此刻更因这冗长无聊的见面流程而显露出几分惫懒,正微微侧首,盯着自己的指甲瞧着,神游天外。
金沉璧仿佛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一瞬的间隙,立刻找准时机,用一种带着恰到好处的仰慕与怯生生依赖的语气,轻声开口:
“早在家乡时,便常听族人说起天朝慕容将军的赫赫威名,用兵如神,保得北境安宁,边境百姓无不感念。”
她话语顿了顿,目光真挚地望向慕容舜华,“今日得见贵妃娘娘天人之姿,英气不凡,方知何为真正的将门虎女,风采令人心折,嫔妾心中甚是敬仰。”
她的赞美并不显得过分谄媚,反而带着一种边陲小国对天朝上将天然的敬畏,以及一种女子对另一种截然不同、耀眼夺目存在的纯粹欣赏与向往。
这番话说得巧妙,精准地搔到了慕容舜华最受用的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