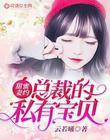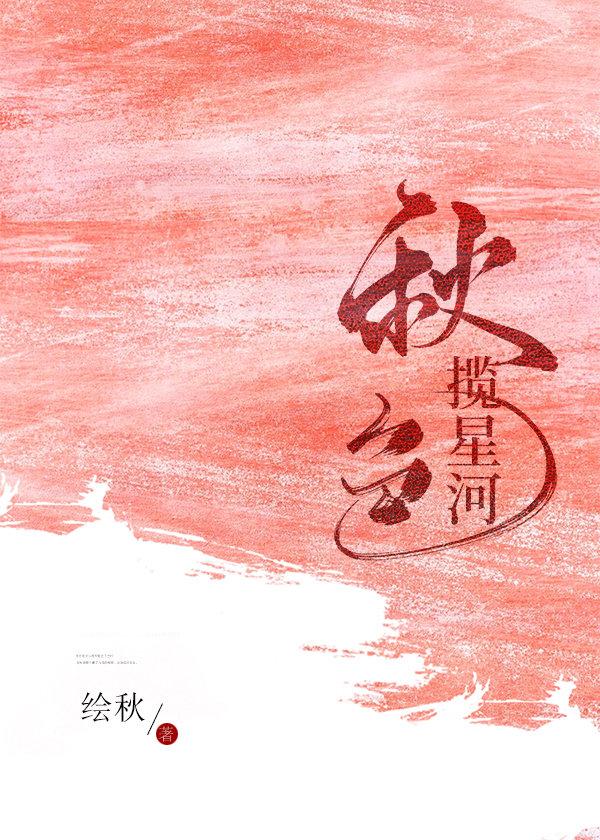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盛唐医缘:穿越女医的锦绣情路 > 池边遇文人吟诗作画显风雅(第1页)
池边遇文人吟诗作画显风雅(第1页)
小船划离湖心亭时,正午的阳光已变得柔和。萧景琰坐在船尾,注视着林薇将采来的桃花小心翼翼地放入竹篮。花瓣上的晨露虽已蒸发,却依然保持着粉白娇嫩的色彩。
“湖心亭的那几位书生,多是长安城内颇有名望的文人。”他忽然开口,打破了船上的宁静,“其中那位身着青衫的,是去年科举的探花郎,名叫沈修文,其一手好字在长安颇为闻名。”
林薇抬起头,回想起方才在亭中沈修文温文尔雅的风范,点头说道:“观其言谈举止,便知是饱读诗书之人。方才他欲邀我们共赏诗词,倒是我打扰了你们的文人雅兴。”
“不必这么说,”萧景琰笑着摇头,“我本就是陪你赏春,与文人应酬不过是其次。不过,若你感兴趣,咱们不妨再去池边的‘墨韵轩’看看,那里常有文人雅集,今日或许还能见到有人挥毫作画。”
林薇眼中闪烁着好奇的光芒。自从穿越到这个时代,她虽然听闻过许多关于文人雅士的传说,却从未亲眼目睹他们作画吟诗的情景。此刻,她欣然点头应允:“好啊,正好借此机会见识一下长安文人的风雅。”
乌篷船缓缓靠岸,两人沿着湖边的石板路向墨韵轩走去。沿途的春色愈发浓郁,岸边的柳树垂下万千柔枝,随风轻舞,仿佛在向行人致意;成片的迎春花在草丛中绽放,金黄一片,与粉白的桃花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绚烂的春日画卷。
墨韵轩坐落在曲江池的西岸,是一座临水而建的雅致楼阁。楼阁外翠竹环绕,风拂过竹林,发出“沙沙”的轻响,显得格外清幽。楼阁内已聚集了不少文人雅士,他们大多身着长衫,有的围坐在桌旁品茶论诗,有的则站在窗边,对着湖面即兴挥毫。
“萧公子!”刚踏入墨韵轩,便有人认出了萧景琰。说话者是一位身着白袍的老者,须发皆白,却精神矍铄,正是长安知名书画家柳承宗。他快步上前,笑容满面地拱手道:“今日怎有空光临墨韵轩?这位姑娘是?”
“柳老先生安好。”萧景琰拱手回礼,侧身介绍身旁的林薇,“这位是仁心堂的林大夫,医术精湛,还在流民安置点开设培训班,教授流民学医自救。今日陪同她来曲江池赏春,便顺道来墨韵轩一访。”
柳承宗闻言,眼中闪过一丝惊讶,随即向林薇拱手致意:“久闻仁心堂林大夫的美名,没想到竟是如此年轻的姑娘,真是巾帼不让须眉!”
林薇连忙回礼,谦逊道:“柳老先生过奖了,我只是尽了医者本分,比起老先生在书画界的卓越成就,实在微不足道。”
柳承宗含笑摇头:“姑娘真是太过谦虚了。医者救死扶伤,造福百姓,这份功绩,远比我们这些舞文弄墨之人更有意义。今日能在此与姑娘相遇,实乃缘分,不如一同坐下品茗,欣赏他们作诗作画如何?”
萧景琰与林薇欣然答应,随柳承宗来到二楼的雅间。雅间临水而建,推开窗户便能尽览曲江池的秀丽风光。桌上早已备好了精致的茶具,柳承宗亲自为两人斟茶:“这是今年新采的雨前龙井,姑娘请品鉴,看看是否合乎您的口味。”
林薇轻轻端起茶杯,浅啜一口,只觉茶香浓郁,回甘绵长,比起平日所饮的粗茶,不知雅致了多少倍。“真是好茶,多谢老先生。”
雅间外的大厅内,几位文人正围聚在一张大案前。案上铺展着一张洁白的宣纸,一位身着蓝衫的书生手持毛笔,正对着窗外的春色挥毫作画。他笔法流畅,寥寥数笔,便将曲江池的湖光山色勾勒得淋漓尽致——远处的湖心亭、岸边的桃林、湖上的游船,无不栩栩如生,仿佛跃然纸上。
“这位是苏明远,长安知名的山水画家,”柳承宗介绍道,“他尤擅描绘春日景色,笔下的桃花格外灵动,素有‘苏桃花’之美誉。”
林薇凑近细观,只见苏明远笔下的桃花,有的含苞待放,有的绽然盛开,花瓣层次分明,仿佛能闻到淡淡花香。她不禁赞叹道:“苏先生的画作真是传神,明明是静态画面,却让人感受到春日的生机扑面而来。”
苏明远听到夸赞,转过头,笑着对林薇拱手致意:“姑娘过奖了。能将曲江池的春色留住纸上,也是得益于这春日美景的恩赐。”
就在这时,另一边传来一阵吟诵声。沈修文手持折扇,立于窗边,正对着湖面吟诵其新作的诗篇:“曲江三月春光好,碧波荡漾映桃红。画舫轻摇随波去,清风送暖入怀中。”诗句浅显易懂,却将曲江池的春日景致描绘得淋漓尽致。周围的文人纷纷鼓掌称赞,有人甚至取出纸笔,将诗句一一记录。
“沈探花的诗果然清雅脱俗,”柳承宗赞叹道,“仅凭数语,便将曲江池的春色尽收眼底,不愧为去年的探花郎。”
萧景琰望向林薇,含笑问道:“林大夫,你以为沈探花的诗作如何?”
林薇略一沉吟,答道:“沈先生的诗清新自然,巧妙地将春日美景与闲适心境融为一体,实属难得。尤其是‘清风送暖入怀中’一句,令人仿佛真切感受到春日的暖风,极具感染力。”
沈修文听到林薇的评价,眼中掠过一丝惊喜,随即走到她面前,拱手施礼:“姑娘竟也对诗词颇有研究?不知姑娘可有佳制,能否与我们共赏?”
林薇微微一愣,随即摆手道:“我只是随口说说,谈不上什么研究,更没有所谓的佳作,怕是要让沈先生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