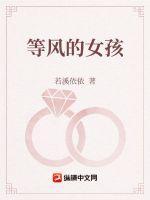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公主永嘉 > 4050(第29页)
4050(第29页)
待那两位军士离开后,秦小山方拿出银针一一试毒。
见他如此谨慎小心,令仪稍加思忖,低声问秦烈:“要杀你的人,是不是太子?”
秦小山闻言,不由抬头看了她一眼。
秦烈并不回答,只平平道:“敢说这样的话,你好大的胆子。”
他语气并不严厉,令仪道:“我思来想去,除了太子,无人再有这样的胆量和手段。”
虽然秦烈连年征战树敌甚多,可那些人不是早已黄土一抔,便是已归顺大宪,万不敢也没必要行这样的事。
便是他们敢,败军如丧家之犬,如何能得知秦烈这样隐秘的行程?
能做到收买内鬼的,满天下唯有皇上与太子,可皇上要杀秦烈,何须这样的手段?
秦烈凝眸看她:“公主不妨说说,太子为何要杀我?”
令仪一字一字道:“功高盖主,储君之争。”
秦烈半笑不笑:“公主以为,我会与二哥争太子之位?”
令仪轻叹:“大位之争,从来不在你想不想,而在你能不能。”
古往今来,文武双全的宗室未必有篡位之心,权倾朝野的大臣也未必有不臣之念。
可一旦他们有可能威胁天子,不反也是反,不争也是争。
否则,昔日她父皇为何对宗室如此严苛?
七皇子更是几乎将宗室子弟屠戮殆尽。
秦烈面色转为沉冷,不发一言。
令仪愈发肯定自己的判断,“如今天下尚未安定,太子便已容不下你,他敢在路上截杀,那京中、焕儿是否也已”
自来大位之争,必要斩草除根,若非如此,谁人要杀秦烈又关她何事。
一想到焕儿可能有危险,她怎能不忧心如焚,坐立难安?
秦烈默了半晌,方道:“不是二哥,是二嫂。”
他自嘲一笑:“她行此事必然瞒着二哥,找的是江湖死士,我死了当然最好,便是不死也不过抛洒些银两罢了。我死了,才到斩草除根那一步,只要我还未死,她便不敢对其他人动手。”
他似乎极为疲累,连语气中也透着萧索。
自古天家无情,可秦家入主皇城也不过三四年,竟也走到了这一步。
令仪不知该说些什么,更不想去安慰什么。
他也并不需要任何人的安慰,萧索之意只在他身上停留刹那,很快又是一副冷峻睥睨的凌人之态……
夜里,令仪在秦烈处守夜。
他躺在床上,她则睡在窗边一个小塌上。
周遭院子都被清空,四周极为静谧,除却油灯照耀那点地方,屋内一片漆黑。
在这般寂静中,屋子又这般小,人的耳力格外灵敏,秦烈的每一次咳嗽似乎都在她耳畔炸响。
令仪听得连自己喉咙也痒起来,只强力忍着,连翻身也不敢,只等他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他呼吸终于平稳,令仪终得闭上眼睛,她今日也极为疲累,可还没等她睡沉,耳边便传来了粗喘声,像风箱一样哧哧作响。她拉起被子盖住脑袋,不愿再听,却挡不住他的低呼。
不同于在驿站时听得模糊,共处一室,她清晰地听到他来来回回梦呓着“不要”,声音沉痛而急切,似乎饱含无数惶恐和伤心。
之后便是低低的呻吟与粗喘,床上不断传来衣料摩擦的声音,久久不曾消停。
如秦烈这样的人,竟也会有梦魇,重逢之前令仪实在想象不能。
可如今只他们两人在这里,他这般模样,她也睡不了。
且不同于在外面的驿站,这样的漆黑寂静,只她们两人在房中。
秦烈如同中了邪一般,似笑似哭,再加上之前刚见过他杀人,令仪不由心生惧意。
她睁着眼睛,胳膊上升起细小的疙瘩,随着他含糊的梦呓愈发恐惧。
如此许久,她无奈起身,端起油灯,来到秦烈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