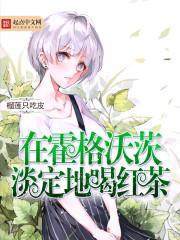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爱情只是她的养料 > 第十五章(第1页)
第十五章(第1页)
半个月的山居时光,像一场漫长而奢侈的沉睡,让被撕裂的神经,得以在绝对的寂静中缓慢地、艰难地开始自我修复的初阶工作。
她依旧疲惫,但至少,那种濒临崩溃的、被无形绳索勒紧喉咙的窒息感,似乎在山风竹韵里,被稀释了少许。
一种极其微弱、近乎本能的冲动,在心底荡漾。
那是对“声音”的重新敏感。
起因是林语某天傍晚带回来一只用竹筒做的简易口哨,吹出的声音清越悠长,带着竹子的天然空灵。
那声音穿过薄暮,意外地没有刺痛谢遥敏感的神经。
她怔怔地听着,久违地,对“捕捉”和“留存”某种声音,产生了模糊的渴望。
几天后,谢遥破天荒地主动开口,声音带着久未使用的微哑:“林语……帮我买套设备。”
“嗯?”正在整理照片的林语抬头,一脸茫然,“什么设备?”
“录音的。”谢遥的目光投向露台外无垠的竹海,“能录下……这些声音的。”
林语的眼睛瞬间亮得惊人,像点燃了两簇小火苗。她没有多问一句“为什么”或者“你要干嘛”,只是立刻掏出手机开始搜索相关科普,仔仔细细地考察了几套设备,随后果断下单,动作快得像怕谢遥反悔。
不到两天,一套便携的专业录音设备就送到了酒店。
那之后,谢遥的“静止”状态里,多了一项内容。她不再只是坐在露台发呆抽烟,而是会在清晨雾气未散,或午后阳光正好时,背上小巧的录音包,戴上监听耳机,独自走进酒店后山那片更幽深的竹林。她的脚步很轻,甚至有些虚浮,像是还没接受现实。
她会在一个地方停下。
可能是溪水潺潺流过的石滩旁,可能是风过竹梢发出呜咽般声响的坡地,也可能是只有虫鸣鸟叫的空旷谷地。
她会安静地站立很久,然后,调整着设备的方向和参数,然后按下录音键。
耳机里,世界被放大、被聚焦:风吹过千万片竹叶,摩擦出沙沙、簌簌、哗哗的层次分明的声响,如同绿色潮汐;
鸟鸣清脆短促,或婉转悠长;
溪水击石,叮咚作响;
甚至能捕捉到远处,山涧隐约的瀑布轰鸣,以及脚下枯叶被踩碎的细碎咔嚓声……
她像个虔诚的采音人,沉默地收集着大自然最原始、最丰富的和声。
没有目的,没有计划,只是单纯地记录。
这过程本身,对她而言就是一种疗愈。
那些纯粹的自然之音,不携带任何人类的情绪和评判,像温柔的潮水,一遍遍冲刷着她被噩梦和喧嚣堵塞的听觉神经。
在专注聆听和记录这些声音时,她纷乱的思绪会短暂地沉静下来,获得片刻珍贵的、纯粹的放空。
回到房间,她有时会将录制好的片段导入电脑,用简单的软件排列组合,形成一段段纯粹的环境音“日记”。
她只是听。
反复地听,在那些声音的包裹中发呆,抽烟,或者沉沉睡去。
她没有尝试去创作任何旋律,甚至没有碰过房间里那架作为摆设的、音色普通的电子钢琴。
录制自然声音,是她目前唯一能做的、与“音乐”相关的、安全而疏离的接触。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
一周后,林语和朋友筹办的服装工作室装修完毕,林语要回北京的家拿些资料,然后飞纽约。
谢遥没多说什么,也打算一起回去。
她的卡依旧被谢聿怀冻结着,她不想一直靠着林语,不想一直花林语的钱——即使她以后可以还上。
在安吉的几次录音尝试让她有了一些信心,她想着回去,或许可以继续这种采音的生活,慢慢来,这样就不需要再通过无谓的购物、酗酒和弹琴,那些不健康的方式来缓冲内心的不安……
万一,能有些转机呢。
她们没有通知任何人接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