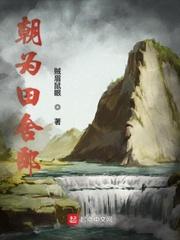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猛兽隔离区(校园1v1) > 62不愿你难过(第2页)
62不愿你难过(第2页)
挣扎到气喘吁吁,他却岿然不动,气定神闲地撑在上方,像在观赏宠物的叛逆期。
宠物身小力微,翻不出什么花更逃不出五指山,所以慷慨地陪它玩一玩幼稚的追猎游戏,待它力竭,摸摸它的脑袋夸它一句good
girl,就知它会摇着尾巴蹭来脚边。
名为情绪的胡同向来没有分叉路,若一条路走到黑势必撞得头破血流,原路折返或许能及时止损。
倪亦南深谙这个道理,却在此刻,在他身下,变得蠢笨又执拗。
与小时候的成长环境有关,倪亦南倾诉欲很低,几近于无,于是她消化负面情绪的方式便是独处。
她需要一个安静且无人打扰的私密空间,手上无止境地去做一些事,或许在冲浪,或许在刷题,或许在翻书。。。。。。
但无论她在做什么,脑子里一定在走神刚刚的事,一遍一遍复盘,一遍一遍拆析,连细枝末节都抠出来反复晾晒,然后洗脑般告诉自己“这没什么”“这算什么”“比这难过的事多了去了”。。。。。。
倪亦南大多时刻是这么做的,时而有用,时而消化不良。
此时,她的状态明显偏向于后者。
大脑防御机制似乎失了效,回想起他这些天明里暗里、言行举止一直在欺负她。
肉体上,精神上,强势又不讲理。
而现在他还要轻描淡写掠过她所求的,将她压在身下,用性爱抹平硝烟。
把她当什么呢?
倪亦南厌恶自己被长辈唤作懂事的乖孩子,厌恶沉迦宴把她当做摸摸脑袋就会蹭上去的good
girl。
即便沉迦宴只是棘手地在想,在事情办成之前,该怎么让他的宝贝消气。
她无从得知,也不会相信。
情绪破盾般爆裂开,神经末梢都在发烫,倪亦南困囚在胡同尽头,眼眶终于盛不下,热泪滚落。
不想两人吵架时,被他看见自己软弱的样子,那好像示弱,像低头。
于是偏开脸。
却意外看清,茶几上倒着一盒套。
为什么这种时刻他还能想到性?
为什么没有解释,没有道歉,只有性?
她是他的什么呢。
肩膀抖颤,情绪突破防线有些不能自已,眨个眼的功夫,垫单晕湿一大片。
“别哭。”
静寂的夜里唯有她难过而压抑的啜泣,沉迦宴放归她小腿自由,抚摸眼角的泪痕,压下去亲吻她。
他说,“对不起宝宝,是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