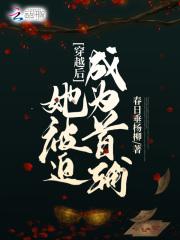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当过明星吗,你就写文娱? > 第二百零七章 狗策划余惟(第3页)
第二百零七章 狗策划余惟(第3页)
离开凉山后,他收到消息:教育部批准设立“平民声音研究中心”,挂靠于中央音乐学院,首批收录的正是“声音档案”前五千份材料。同时,《小人物》被译成英文、法文、阿拉伯文,在多个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演出。国外媒体称其为“来自东方的平民史诗”。
但他并未因此停下脚步。
进入贵州黔东南,他走进侗族大歌传承基地。一位八十岁的歌师拉着他的手说:“我们唱了几百年,都是神仙鬼怪的故事。现在你们开始唱活人了,真好。”
余惟请教如何用侗族多声部形式表现现代劳动者。老人沉思良久,领他到村口古井旁:“听,挑水的女人走路有节奏,舀水有声响。这就是我们的节拍器。”
于是,他尝试将快递员、护士、乡村教师的故事融入侗族大歌结构,创作出实验性作品《人间和声》。当十二位侗族妇女用母语齐声唱出“她防护服穿了十二小时,只为守住一个病房的温度”时,现场所有人泪流满面。
此时,距离他最初离开武汉,已整整三年。
这三年里,他走过二十七个省份,收集口述故事一千三百余则,创作歌曲四十六首,其中二十一首被民间广泛传唱。他的脸不再出现在娱乐新闻,却频繁出现在纪录片、公益广告和社会学论文中。有人称他为“行走的时代录音机”,也有人说他是“当代民谣诗人”。
但他始终记得那个甘肃车站的老人说过的话:“我们不怕默默无闻,就怕被彻底忘记。”
春天再次轮回之际,他回到北京,应文化馆邀请参与“声音档案”成果展策划。布展期间,一名志愿者小姑娘怯生生递给他一封信。
“这是我奶奶写的。”她说,“她不识字,是我帮她录的音转成文字。她说,如果还能被听见一次,她就想说这些。”
信很短:
>“我老伴是抗美援朝回来的炊事兵。一辈子没打过枪,可他说,战场上饿不死一个战士,是他最大的功劳。他去年走了,墓碑上只刻名字和生卒年。我没文化,说不出伟大,就想知道??有没有一首歌,也能唱唱做饭的人?”
余惟握着信纸,久久不能言语。
当晚,他在展馆角落架起麦克风,对着录音设备轻轻唱起一段即兴旋律:
>“别人讲英雄跃出战壕,我说炊烟升起才是胜利的号角
>他背着锅行军三百里,雪地里炖出一碗热汤面的味道
>没人记得他的编号,可每个活下来的士兵都记得??
>那一口温热,曾把死亡挡在了黎明之前”
这首歌后来叫《无名灶》。
展览开幕那天,人流如织。人们在耳机前驻足,聆听矿工的喘息、纺织女工的哼唱、乡村邮递员的脚步声。一面墙上滚动播放着普通人照片与话语:“我只是想让孩子读完书。”“我修了四十年铁路,没出过一次错。”“我每天扫街六公里,我觉得我在守护这座城市。”
一位记者问他:“你觉得这一切有意义吗?”
他望向展厅中央一群小学生正围听着一位退休清洁工讲故事,答:“意义不在结果,而在过程。就像种子落地,你不知道哪一颗会长成树,但你必须先撒下它们。”
数月后,西藏那所牧区小学传来消息:孩子们集体录制了一首歌,用藏语翻唱《小人物》,并寄来一张合影。照片上,每个孩子手里举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一个普通人的名字??阿妈、阿爸、老师、医生、护林员……
余惟把照片贴在笔记本首页,继续踏上旅程。
这一日,他行至内蒙古草原边缘的一个小镇。黄昏时分,坐在加油站旁长椅上休息。远处风车缓缓转动,天空铺满霞光。一位加油站女工走过来,递给他一瓶水。
“你是不是余惟?”她问。
他点头。
她笑了笑:“我丈夫是货车司机,跑了二十年长途。去年车祸走了。我听他最后一遍放的歌,就是你的《归途纪事》。”
余惟心头一震。
“我想告诉你,”她声音平稳,“那天晚上,他听着听着,笑着说了一句:‘原来我也算个英雄啊。’”
风吹起她的工装衣角,夕阳把她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余惟站起身,深深鞠了一躬。
他知道,这条路依然漫长,但他已不再问终点在哪。因为他终于懂得: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铭记;每一首歌,都是一座无形的纪念碑。而他所能做的,就是继续走下去,把更多未曾发声的名字,轻轻放进旋律里,让它们随着风,流向时间的下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