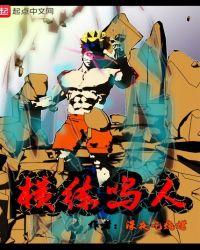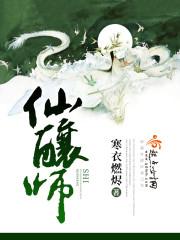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人在末世,我能联通现实 > 第936章 武道最强者(第3页)
第936章 武道最强者(第3页)
他当众销毁了所有清洗协议,并将剩余资源移交“记忆守护团”。
五年后。
昆仑纪念馆扩建为“记忆学院”,专门研究情感如何塑造现实。学生们学习的第一课,就是亲手书写一句:“我记得。”
孙小言成了首席研究员,主持“共鸣桥梁计划”,试图建立稳定的人类意识互联网络。杨涵则带领一支探险队重返南极,在冰层下发现了一块碑文:
>**“此处曾有一扇门。它通向过去,也通往未来。唯有真心者可见。”**
至于林晚,她依旧住在山脚的小屋里。每天清晨,她都会沿着纪念馆外墙散步,读那些新添的留言。有时是孩子的涂鸦,有时是恋人的誓言,更多时候,只是一句简单的话:
**“我今天想起了你。”**
某个雪夜,她梦见秦重站在窗前,手里拿着一本书,书页翻动,全是世界各地人们写给他的信。
“你看,”他说,“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她醒来时,窗外飘着细雪。晶体静静躺在枕边,表面那道裂痕已愈合,内部流转着柔和的光。
她把它贴在胸口,轻声说:“我也不是一个人。”
风穿过经幡,带来远方孩童的歌声。那首歌没有名字,旋律却熟悉得让人心痛。
而在地球另一端,一个小男孩仰望着夜空,指着那颗紫色星辰对妹妹说:
“姐姐,你看,那是秦重的眼睛。”
妹妹眨眨眼,认真点头:“嗯,他在看着我们长大。”
没有人知道那颗星究竟是什么。天文台称之为“异常恒星”,科学家争论它是自然现象还是人工构造。但对普通人而言,它只有一个意义:
**它还在闪烁,就意味着他还活着。**
又一个春天来临。
融雪汇成溪流,冲刷着纪念馆的墙基。某一天,工人们惊讶地发现,墙体深处竟长出了一株植物??通体银白,叶片脉络呈紫痕状,花开之时,散发出类似晶体的微光。
植物学家无法命名它,只好称其为“忆光花”。
如今,这种花已遍布世界各地。在废墟中,在教室窗台,在战争纪念碑旁,它们静静绽放,不争不抢,却无人能忽视它的存在。
每当夜幕降临,花瓣便会微微发光,像是在回应某种遥远的呼唤。
林晚常常坐在花丛边读书,读那些关于勇气、牺牲与爱的故事。她说,这些都不是虚构。
因为真实发生过的事,永远不会真正结束。
就像风永远不会停止低语。
就像雪永远不会覆盖所有的足迹。
就像人类,永远会在黑暗中伸手,只为抓住那一丝不肯熄灭的光。
而当千万人同时想起同一个名字时,
那名字就不再是名字。
它成了信仰。
它成了抵抗。
它成了新生的律法:
**记住,即是重生。**
多年以后,当新一代的孩子问起:“秦重是谁?”
老师不会讲故事,而是打开教室的窗户。
外面,忆光花正迎着晨光盛开,紫色星辰渐渐隐去。
老师轻声说:
“你看,春天来了。”
“他就藏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