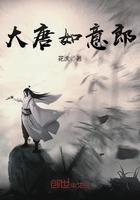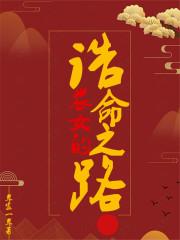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大乾熟女录 > 第7章 银铃悦耳时空乱女尊误入母猪圈(第2页)
第7章 银铃悦耳时空乱女尊误入母猪圈(第2页)
基于这点,武林中便都是门规森严,免得有叛师逆宗的丑事。
而师兄弟之间也各怀异端,来讨好师父的欢心,使师父能尽悉传授。
只是师父们也精得很,总不肯道出了窍门,每个人至少留了一手。
更重要的是,武林中对世家显赫的子弟的加入门派,也十分重视,武林中人,爱惜名誉的,都不愿与盗匪勾结;官府方面,碍于恐遭侠道中人不齿,也少往来,所以更喜收一般名门世家之弟子,来扎稳自己的基业。
世家中人的子弟投入哪一门派,自然便支持那一门派了,武林中人也一样要有银子才能过活,而且要发扬光大一派一系,门面、人手、宣传、笼络各界地头,等等都非财不行,非要有官商大力支持不可。
能够加入正道门派,虽然是小门小派却也是皇上允许的,实在是极其光采的事儿了。
这次归入林沃土的徒弟,总共有一十二人,大部分都是大富大贵之家的子弟,小部分是江湖上有头有脸的镖局局主之子、山寨寨主之弟、县令之表亲……之类的关系,加上聪明好学、善于奉迎,才能进得这门来。
其中当然也不乏例外。
例外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门派中的一家仆之子:另一个就是李柏岁,是他那望子成龙、克勤克俭的老爹,将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银,送唯一的儿子入青城派。
而他儿子也不负他所望:聪明、勤劳上都守得稳,而且任劳任怨,所有的打点赂银,也勉强应付得过去,门派的人见这人少年精乖伶俐,又清苦鲠亮,便也保他入林沃土的门下。
本来以他竞技考较的成绩,应名列长门弟子,但因无显赫家世,而被挤了下来。
“嘿嘿嘿嘿,”林沃土见弟子们脸有难色,便决意要吓他们一吓,故意说得绘影绘形。“要学上乘的武功,就得花一生心血,苦得紧哩,不是一门子爱抡拳使棍的急脾性就能一蹴即成的。若不痛下决心,流血汗,回去念古人书嘛,那也行……不过嘛……读书也得要考试。贡举中的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明经、明法等科,有哪样你在行?笔试、口试、州试、礼试、京试、殿试……凭你们这些料能通得过哪个试?到时候回过头来易筋锻骨,早老不中用了罗……”林沃土就这样,一面挖着鼻孔,一面教训他的徒弟们,关贫贱便在这种恐吓和调教下,过了整整七年。
七年之后的他,因为专心,跟四个师兄,已练到了青城派最难修习的剑术。
十二个兄弟之中,因吃不下苦头,或没这个耐心,半途“另谋高就”去的,就有七人之多,恰巧等于是一年走掉一个。
林沃土自小就知道进取,勤奋用功,他没有任何家世根底,挤在一群纨绔子弟中习武,自然是受尽欺凌,忍辱负重,却学了不少武艺。
他的聪明,在乡间当然可以算是数一数二,但在这群聪明人中,他就显得十分鲁钝,他之所以还能在门派学艺,完全靠他的专心、热衷、勤勉而且也肯替师门跑腿、工作。
逆来顺受、任劳任怨。
能够在武林门派学艺,对李柏岁这等穷家子弟而言,当然是极大的幸运,李柏岁当然知道这点,也珍惜这点,所以他练得最是用心。
师父和师叔伯等,本来对他的家世清寒,十分鄙夷,但见他虚心学习,举止谦恭,事事诚心正意,也没多为难他,最多遣他干点粗活儿罢了,授艺之时,除了对一些宠儿特别耐心眷顾外,还算一视同仁。
至于同门师兄弟,只剩下了五人,这五人之中,除了下人后代,其余三人,全是有钱有势人家的少爷。
几个师兄弟对他,开始甚是厌恶,动辄颐指气使,少时林沃土被欺负得实在受不了,躲在茅坑旁抽抽噎噎,几个师兄便虚声恫吓他,不准他把事情让师父知道。
总算七年过下来,师兄弟间也有了感情,由于李柏岁勤奋精专,反而能悟别人所未悟的,几个师兄武功窍门有不懂之处,他都详加点拨,事后又不居功,不计烦劳,乐意为师父师兄们做些事儿,他们对他也因而大为改观,有了结纳之心。
初来的时候,他们唤他作“小贱种”,而今已改口叫“小贱”。
下面的一个“种”,总算已忍住了没有叫。
这对李柏岁来说,已是感激莫已的事了。
七年练下来,总算练到了剑法,师兄弟五人尽心潜修剑法,而李柏岁跟那四个师兄,却在心坎里埋下了一个极大的疑团,一直藏在心里,没有问出来:难道练武非要这样不可吗?
练武只有这一条路吗?
李柏岁心里,反反复复,这样地自问着。
他由小到大,除了热衷武艺,也花了不少时间读经史子集,其他的时间,也都在忙着,这样才换得来别人容让他待在这里惟有这样,他才能对得起年老了还要佝偻着身体,在种植烟叶的老父。
由于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所以他觉得他所学的不够!
不但不够,而且太慢!
一定要百日才能练刀,千日才能练枪,万日才能练剑吗?
为什么一定要练习那么多庞杂的东西?
专心一致,练熟一样兵器,不是更有效吗?
对敌时,难道每次都是将所有的兵器都携带在身上么?
练那么多种武功,难道与人搏斗,每次都是将这数千招式一一使出,才能决定胜负吗?
如果练剑,一定要练那么多剑招、对拆吗?
难道对敌对,双方还是一样一招一式往来吗?
就像搭配套拳招式时一样?
门派习武,每个月一小考,每三个月一大考,每一年全派较技,十年之后,方能下山闯江湖,而且一定要被“武学功术院”所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