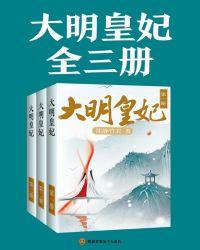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都重生了谁考公务员啊 > 第650章中国最顶级的车牌(第1页)
第650章中国最顶级的车牌(第1页)
“易小姐。”
陈着起身打个招呼。
能在首都地头上还这么蛮横,并且和陈着认识的,只有易保玉。
但是格格并没有搭理。
可能是天气有点冷的缘故,她裹着一件长及小腿的厚风衣,鸭舌帽压得。。。
夜雨敲打着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江辰坐在空荡的办公室里,手指在键盘上缓缓停顿。窗外的城市被雨水洗得模糊不清,霓虹灯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拉出长长的光带,像一条条通往未知的路。他刚发完一封邮件??《“破壁计划”第一阶段执行方案》正式提交至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及三家合作高校的课题评审组。
附件足足有四十七页,从项目背景到技术架构,从样本追踪模型到伦理审查机制,每一个字都是他与林晚晴熬过十几个通宵打磨出来的。而最核心的部分,是他们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非登记人口教育权动态补偿机制**。
这个机制试图回答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当一个孩子因为父母务工流动而频繁转学、失学甚至从未注册学籍时,他的受教育权利该如何追溯与补救?传统政策只关注“在校生”,但“萤火计划”三年来的数据表明,全国至少有三十八万儿童处于“教育真空地带”??他们不属于任何学校的统计范畴,也不在任何政府数据库中留下痕迹。
“我们要做的,不是等他们走进教室才开始记录。”林晚晴曾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说,“而是要让系统主动去找人。哪怕他在渔排上、在集装箱屋里、在凌晨四点的菜市场帮工,我们也该知道他是谁,他需要什么。”
江辰合上电脑,起身走到窗前。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林晚晴发来的语音:“明天上午九点,南沙码头见。陈老师带着两个孩子转到了广州番禺,家长终于同意让他们入读安置学校。我们去接他们,顺便做入学适应评估。”
他回了个“好”,又补了一句:“带上相机。”
第二天清晨,天边刚泛起鱼肚白,江辰已驱车抵达南沙港。林晚晴早已等候在码头集装箱堆场旁的小路上,穿着浅灰色冲锋衣,背着双肩包,手里拎着一袋热腾腾的肠粉。她看见他下车,笑着递过去一份:“给你留的,加了双蛋。”
“你几点到的?”他边吃边问。
“六点半。”她揉了揉眼睛,“昨晚梦见那个叫小舟的女孩又不上学了,吓醒后干脆不睡了。”
小舟是渔排学校里年龄最小的学生,七岁,瘦得像根芦苇。母亲患尿毒症,靠父亲远洋捕鱼维持透析费用。去年冬天,她曾连续两周缺席课程,后来才发现她每天凌晨三点就要起床帮忙分拣渔获,白天困得趴在桌上写作业。江辰和林晚晴协调当地社工介入,才让她重新回到课堂。
不多时,一辆破旧的面包车驶来,车身上贴着“海星公益助学”的标志。车门打开,陈老师率先跳下,随后牵出两个怯生生的孩子??正是小舟和比她大两岁的哥哥阿磊。
“他们昨晚十一点才从阳江赶过来。”陈老师低声说,“一路上换了三趟车,妈妈本来不想放人,说是怕进了城就再也回不去原来的生活。”
林晚晴蹲下身,轻轻抱住小舟:“你现在要去的地方,不会让你一个人扛所有事了。”
前往番禺安置学校的路上,江辰坐在后排,看着两个孩子透过车窗第一次看到城市高架桥时惊愕的表情。小舟忽然转头问他:“哥哥,这里的学校也有海吗?”
“没有海,但有图书馆、科学实验室,还有能教你画画的美术老师。”他说,“你想学画画吗?”
她点点头,声音很小:“我想画妈妈醒来的样子。”
那一刻,江辰觉得胸口像被人狠狠攥住。
抵达学校后,校方安排了一间临时教室供他们进行心理测评与学习能力测试。江辰负责操作AI测评系统,林晚晴则用温和的语气引导孩子们完成问卷。结果显示,尽管长期缺乏系统教学,小舟的语言理解能力和逻辑思维水平竟接近城市同龄儿童平均水平,而阿磊的数学天赋尤为突出??他在一道初中奥数题上的解法,甚至比标准答案更简洁。
“这不是奇迹。”林晚晴在笔记上写道,“这是被压抑的潜能,在极端环境下依然顽强生长的证据。”
中午,他们在学校食堂吃饭。校长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姓李,说话直率:“说实话,刚开始接到你们的通知,我以为又是那种拍个照走人的‘慈善秀’。但现在我信了,你们是真的想把这些人‘找回来’。”
“不只是找回。”江辰说,“是要重建他们的身份。”
下午两点,入学手续办妥。小舟穿上崭新的校服,站在镜子前看了很久,最后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左胸口的校徽。
返程途中,林晚晴接到博士导师的电话。对方语气严肃:“教育部有个青年学者专项扶持计划,今年首次向民间研究团队开放申报。我推荐了你们的课题,但要求项目负责人必须具备博士学位或副高以上职称。你现在延期入学,等于自动失去资格。”
车内一时沉默。
“老师……”她轻声开口,“如果我不读博了呢?”
“你说什么?”导师几乎提高音量,“你知道多少人挤破头都想进这个圈子?你以为田野调查就是学术?没有理论框架、没有方法论训练、没有发表渠道,你那些感动人的故事最终只会变成朋友圈转发三次就没人记得的鸡汤!”
林晚晴握紧手机,指节发白:“可如果我的研究不能改变现实,那它本身就该被质疑价值。”
“你可以两者兼顾!”导师叹气,“别让情绪绑架理性。”
挂掉电话,她靠在座椅上闭目良久。江辰没有说话,只是将车载音响调低了些许。
三天后,他们在深圳召开“破壁计划”启动发布会。地点选在一栋老旧工业区改造的共享空间,台下坐着二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公益组织代表、乡村教师、流动儿童家长,以及几位低调出席的教育部观察员。
江辰站在投影幕布前,身后播放着一段纪录片片段:甘肃黄土高原上的母女徒步十公里上学;深圳城中村出租屋里,三个孩子共用一张折叠桌写作业;海南渔排上,孩子们举着平板电脑跟着直播课朗读英语……
“我们常说教育公平。”他的声音沉稳而清晰,“但我们很少问一句:谁定义了‘公平’的标准?是谁决定哪些孩子值得被看见,哪些可以被忽略?”
台下有人悄悄抹泪。
“今天,‘破壁计划’正式启动。我们将联合三十所基层学校、十二个公益机构,在未来两年内建立中国首个‘流动儿童教育追踪数据库’,覆盖十万名非户籍学生。每一份数据都将匿名化处理,并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边缘群体教育生存报告》。”